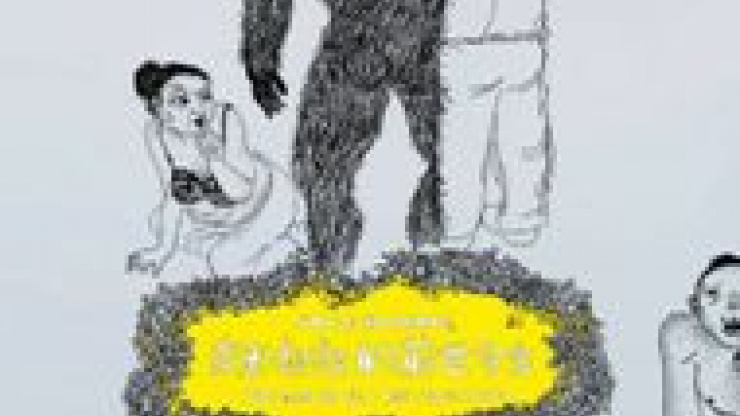再看「東南亞」:專訪陳翠梅導演

自2006年以《愛情征服一切》(Love Conquers All)接連在鹿特丹影展與釜山影展拿下金虎獎與新浪潮獎之後,陳翠梅儼然成了馬來西亞乃至東南亞電影在國際嶄露頭角的領航代表。她與李添興、劉城達、阿米爾・穆罕默德(Amir Muhammad)於2004年共同創辦的「大荒計畫」,成功帶起一波「馬來西亞新浪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每隔幾年,陳翠梅的作品也會在台灣放映,引發討論。今年非常巧合地,五月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的「憂傷似海:東南亞真實之浪」(SEA of Sadness)專題選映了她的長片作品——《無夏之年》(Year without a Summer,2010),七月台北電影節邀請她出任國際新導演競賽評審,接下來八月桃園電影節為其策劃「焦點影人」專題,共放映她的六部短片與兩部長片,台灣觀眾可說是相當幸運地得以在這三、四個月間密集與陳翠梅接觸。
這樣的巧合自然也反映台灣大大小小影展這幾年愈發將目光投向東南亞的趨勢,舉凡當代敘事影展三屆以來的相關單元、 2017 年台北電影節的「未來之光:東南亞新勢力」、2018 年台北電影節的「亞洲稜鏡:GDH 559」與「無畏,因為有所謂:東南亞新銳短片選」、於政治大學舉辦的「一部電影,一個旅程2——關於東南亞電影的五個提問」,以及前段提及的幾個影展單元等等,皆可見近年東南亞電影從過去影展普遍不敢碰觸的票房毒藥,搖身成為大家爭相想一探究竟的區域,且除了放映,也衍生出多場延伸論壇。
從這幾年影展相關論述與訪談,我們或許可以快速抓取出「獨立」與「連結」兩個常見的關鍵字,前者針對現實的突圍,後者關於區域的合作。兩者相當程度地回應了台灣電影圈,在影像生產與製作層面上想像與借鏡的策略,以及在政治與文化孤立狀態下的擴張與融入慾望,一種帶著方向性與目的性的觀看。亦即當影展開始向觀眾介紹東南亞電影時,似乎是依循著某種理解脈絡,自有既定的關注與對話面向。於是,究竟我們如何在這樣的基礎上再打開,還能如何觀看東南亞/東南亞電影,又東南亞自己怎麼觀看彼此,以及回應我們的觀看,或許就成了逐步「看見」之餘,我們更急需深入探討的。且當我們逐漸強化「東南亞」作為一個整體文化場域,進行影像的閱讀,這樣的策展又鞏固與服務了什麼?內部差異與衝突如何在策展中被置放、凸顯或忽略?
對此,我們特別針對「觀看」這個面向,與陳翠梅進行請益交流(注1)。
——可以先請您回憶一下自己這十多年來跟東南亞電影人交流互動的情形嗎?
最開始的時候,東南亞的電影節很少,所以我們很多是在歐洲的影展上認識的,尤其是鹿特丹,另外是釜山,這兩個是一定會碰面的地方。葛江(Gertjan ZUILHOF)算是歐洲選片人中最早開始做東南亞專題的(注2)。2005 年他在鹿特丹做了一個「SEA Eyes」單元,我們很多人因此認識,然後在各種影展上常聚在一起,可能也是性格比較接近,會一起玩,然後會有一些合作。
——十多年來交流越來越頻繁後,自己會感覺到什麼既有邊界的鬆動嗎?
有一些很直接的,比如一個馬來西亞的朋友就跟一個菲律賓的 producer 結婚了,他後來就一直在菲律賓拍電影。這對他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在馬來西亞可能沒有這種機會,他在菲律賓可以跟 Lav DIAZ 或各種導演合作,馬來西亞這幾年都沒有這種比較重要的導演作品;2013 年,我拿到一筆錢拍了《南方來信》,找了當時還沒有那麼有名的趙德胤還有一個泰國導演(編按:Aditya Assarat)各拍了一段,後來泰國導演就監製了趙德胤的《再見瓦城》(2016),這些都是從非常重要的互相認識開始,慢慢發展出來的。
——會這樣問也是因為過去台灣理解東南亞電影,比較多還是從國族的角度出發,或者像過去台北電影節每年都會選擇一個國家作專題,但是現在會愈發的將「東南亞」視為一個集體去認識。當然東南亞電影彼此有交流也有差異,您自己怎麼看東南亞電影以及各自在不同島鏈上的遠觀?
每個國家肯定有不同的文化,我們很常說菲律賓是我們東南亞的拉丁美洲,我們其實很常開他們玩笑,像那個泰國導演就很喜歡說菲律賓的東西難吃,都是給美國人搞壞的。這之中的確有很不一樣的,但也有一個比較接近的,就是東南亞導演很自然、很常有的那種 relaxed(輕鬆)狀態,然後就一起玩,好像是一個特質吧,這是其他國家很少見的。所以我們十多年前出國的時候,東南亞人常會開玩笑那些中國導演苦大仇深,拍的戲都特別長,或者語言不通的日本導演如何如何,但當然現在年輕的導演不一樣了。我不知道是從泰國還是哪邊傳過來的,你知道有一個 t-shirt 的 slogan 叫「same same but different」,我們就是這樣子看我們自己,一樣但也不一樣。
——雖然說國界在逐漸鬆動,但大家還是常從既有的國族電影傳統或既定的區域想像來理解彼此,比如菲律賓的「街頭電影」、「貧窮電影」或泰國的森林等,若從產業面向切入,也可以看到不同的物質條件與結構差異。您自己又是如何從對彼此電影/產業的想像與理解中學習?
我們最早認識時,最大的刺激就是像比如卡文(Khavn DE LA CRUZ)三天就可以拍完一部長片,然後一年可能可以拍九部長片這種,菲律賓就連一般工業體系中的商業製作,也可以在六天內拍完,成本大的話可能十多天;還有比較特殊的,像他們有幾個電視台每年會舉辦電影節,固定提供導演獎金拍電影,剛開始的時候是「Cinemalaya」,一年會選十部,一部75萬菲律賓披索(約 1 萬 4000 美金),拍完了會在「Cinemalaya」播放,就這樣鼓勵了很多新人;另外,他們每年在聖誕節檔期,戲院只准放菲律賓電影,於是很多製作就可以從這個檔期賺回一些錢(注3)。這些都是菲律賓特有的,我們只能討論,沒辦法真的去學,沒有人真的能像菲律賓人那樣三天拍完一部電影,但是它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刺激,至少我們不會說這是不可能的事。這些都是我覺得特別有用的,我們現在辦工作坊也特別喜歡請菲律賓導演來,要不斷讓年輕導演認識菲律賓這種低成本、與朋友共同完成的電影生產模式。當然菲律賓也有問題,就是拍戲拍死的人很多,去年就有兩個朋友死掉。
泰國有泰國的特殊環境,他們也有很好的 studio(片廠),這些 studio 會比較積極的去發掘新人,有很多不錯的新導演作品出來。印尼也是有比較健全的工業,馬來西亞可能就還沒有,所以我們的工作坊就是想讓他們認識,其實在這種產業下你還是可以拍出某些電影。柬埔寨、越南這幾年出了很多導演,比如 Davy Chou(周戴維)那班「Anti-Archive」,這些也都很容易給年輕導演帶來啟發。(注4)
——延續來談,雖然這之中愈發有流動性,既有國族想像可能正在消解,但某程度上又開發、鞏固或強化了某些本質想像,尤其從台灣或西方的角度觀看可能也有其局限,或狹隘的從比如阿比查邦(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的電影中揀選自己所認為的「東南亞性」,扁平的套用在對其他東南亞電影的理解上。
這肯定是有影響的,當你看到(阿比查邦)可以把森林拍成那個樣子,因為我們環境都很接近,我覺得那是必然發生的。但它必須是有各種各樣的,比如說也有Lav DIAZ,也有Brillante MENDOZA(布里蘭特・曼多薩),也有何宇恆。當有各種各樣的電影時,年輕導演比較可以看到,然後想像原來我可以這樣拍,而不是只有一種可能。現在其實出現很多很有趣的菲律賓電影,當然有一些可能受阿比查邦影響,有一些我看起來受到賈樟柯的影響,有一些受到當代藝術的影響,有愈來愈多裝置性的作品,好像是有一股什麼在那邊,但因為我自己沒有太去認識他們,我不知道他們是從哪裡出來的;比如說 “Another City”(《越南迷情》,2016)的導演(PHẠM Ngọc Lân,范玉麟),包括他新的長片(Cu Li Never Cries)的製片(編按:潘黨迪),他們這些人都有這樣的感覺。而像你講的看到阿比查邦,有時候也是受限於你們的選片人可能比較喜歡,他們會這樣選擇,但是其實東南亞電影百分之九十都不是這樣,所以有時候也是選片人的想像。
——台灣這幾年越來越積極的想要做東南亞電影專題⋯
你們自己是怎麼看這樣對東南亞的 interst?
——雖然可能從過去的不看或看不到,到現在可以看到越來越多不一樣的作品,但是在討論上,似乎尚有局限,比如政治上會不斷圍繞審查議題,難有更深入的比較或歷史化分析。或比如美學上大多跟隨西方追捧的幾個導演,進行遲到的認識。有很多東西是我們還沒能更加理解的,會有一種影片逐漸來了,但論述還沒到位的狀態。
我以前來台灣會覺得台灣人對東南亞是不感興趣的,甚至歧視東南亞文化,觀眾也更願意去看歐美電影。但是這幾年我們東南亞強烈感覺到,有很多尤其是韓國、日本的資金要進入或資助東南亞,我們對此會有個戒心,想說那是因為中國那邊沒市場,你們現在想要來了。當然這可能是一個機會,他們終於開始對東南亞感興趣,因為在現在的大環境下,這是他們必須了解的一個市場,也包括他們想要輸出自己的文化。所以我們從三、四年前就看到這個突然而來的 interest,包括中國,也開始對東南亞很感興趣。
對於東南亞本身,我可能真的第一次比較自覺地做東南亞的東西就是《南方來信》吧,因為那是中國網站出資(鳳凰視頻),所以還是要有關於東南亞華人的話題。可能我們一直都互相好奇,當然對我來說,我對馬來西亞有一種想像,不過我的想像跟其他的馬來西亞人可能不一樣,對東南亞的想像肯定也會有這樣的落差。我在拍《南方來信》之前,對緬甸是完全不了解的。而且我們以前講東南亞就是「南洋」,緬甸、越南等是不被包括在內的,所以那時候,我甚至覺得緬甸好像不應該被加進來。
——後來您自己對東南亞想像或理解的逐漸擴張是出於什麼認識?
因為開始認識朋友,我覺得那個是最重要的,交朋友可以最快地打破固化模式,有了朋友之後,發現原來你跟我想像的你不太一樣。比如我們馬來西亞人本來對緬甸的想像就是難民,就算他們很多人也在馬來西亞生活,上餐館吃飯時,還常常會遇到緬甸人 serve(服務)你。
每個東南亞國家的情況也很複雜,像我最先認識的緬甸導演是趙德胤,但當後來我去緬甸作工作坊,或是在韓國釜山那邊的工作坊又再認識其他緬甸導演時,跟他們說起趙德胤,他們會說他不是緬甸人,因為那個國家複雜的歷史與文化背景。越多認識後,你就會發現原來自己真的了解很少。就馬來西亞來說,我們跟印尼還有新加坡有很多共同的歷史,會知道比較多。但比如說泰國、越南相對就少,我們從小對越南的很多知識,都是從看美國電影學來的,至於其他地方就認識更少了。開始接觸這些人之後,對他們的歷史文化還是不完全了解,很多時候還真的是電影讓我們更深的去認識那個國家。
——您剛說對馬來西亞的想像和其他人想像的落差為何?
我覺得馬來西亞可能比其他國家複雜,因為有不同的文化族群,各自受到不同地方的影響,包括回教、印度、英殖民等等。光就華人來說,光譜上有一些也是相當保守,並非完全西化的。於是,我們雖然同樣在討論馬來西亞,談的卻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當你看了三部馬來西亞的電影,它們可能長得完全不一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2005 年第一次去鹿特丹,影展總共選映了四部馬來西亞電影,其中一部是我監製的一個印度片(Chemman Chaalai),整部電影就是在橡膠園裡面的一家印度人;一部是 U-Wei Haji Saari 的馬來片(Buai Laju-Laju),重拍了「The Postman Always Rings Twice」;一部是李添興的《美麗的洗衣機》;一部何宇恆的《霧》。我那時候會想像,如果我是荷蘭觀眾,同時看了這四部「馬來西亞電影」,你會不知道馬來西亞到底是什麼,每個人都有他想像的馬來西亞。但是我又特別討厭那種刻意強調多元文化特質的電影,強化馬來西亞特質,其實我們每個人看到的馬來西亞是很不一樣的。
——這其實也滿接近台灣現在在看東南亞的某種狀態,我們看到了很多完全不一樣的東西,從中去揣想東南亞是什麼。
只能看到片面的,我會覺得被看到的可能像是一個農村的東南亞吧。如果你只看到何宇恆的電影,你不知道馬來西亞還有另外一面;如果你只看到 Yasmin Ahmad(雅絲敏・阿莫)的電影,很多人會覺得馬來西亞電影應該就是這樣,有一種多元性。但是我覺得那也是虛假的,因為真正的生活也不是這樣,真正的生活真的就是分開的,異族戀還是比較少數。所以如果大家因此說馬來西亞電影就是這樣,那個也是假的。
——「東南亞」這個概念與劃分本來就非常複雜,有殖民的各種慾望構造,是個暫時的外來區域整合概念,您自己怎麼將其內化,尤其當別人給定您這樣的身份標籤時?
因為Netflix開始進入東南亞,他們的總部設在新加坡,之前出來談的時候就說東南亞包括台灣、香港,我們那時候聽了就有點驚訝,所以現在台灣、香港也是東南亞?我就開始問起朋友「東南亞」這個詞本來是從哪裡來的,其實也是從美國來的,所以它本來也就是一個假的東西。
我覺得對東南亞的認同當然是一直都有的,但從小我們講的是南洋,是這些海洋的島國,以前所謂「下南洋」的地方,那是我過去理解的東南亞。但現在開始往北上,版圖越來越大,加入了緬甸這些我們以前完全不認識的地方。現在緬甸就在我們的身邊,開始是我們的一部份了,緬甸人在馬來西亞的人口比例很高,尤其在城市中。
——那像您後來也嘗試往中國發展,這也會是您所想像的擴張,或者更多的流動與交流可能嗎?(注5)
我覺得可能在創作上,我一直都是用中文,中國算是一個我比較容易去的地方,我在中國也比較容易被欣賞。我在中國最大的感受,是中國對我的包容性很強,人家不會知道我是外國人,可能只會覺得我是從南方來的。這跟我在台灣的感覺很不一樣,雖然我說中文,但是他們很快就會問你是不是香港人,還是新加坡人等等,沒有那麼包容。
——您是有自覺自己在中國比較被肯定嗎?這可能是什麼原因呢?
我覺得主要是語言或文化,我不知道,就是比如說我寫的東西、我的電影在中國比較多被看到,很常遇到別人說看過我的作品。包括後來在國外比如遇到的韓國人,可能因為他們政府機構請的人是從美國學電影回來的,他們就會說大學做亞洲研究看過我的電影什麼的,我聽到總是很驚訝,因為在馬來西亞就很少遇到,在馬來西亞其實很少人看我的短片或者我的微小說。
——這也跟我們的認識的落差有點類似,像我們過去熟悉的東南亞導演,像是您、曼多薩、阿比查邦這幾個代表,現在這些影展的專題開始擴展之後,也才驚訝還有其他人。或說比如我們對馬來西亞導演的認識,還是比較停留在華人,對馬來人的作品可能只有雅絲敏・阿莫稍微深入一點。
其實我們也是一樣,如果我們不認識其他人,只看過侯孝賢、蔡明亮的電影,那對台灣的想法也就只會是這樣。
——這幾年又再把重心轉回馬來西亞了嗎?
其實我很願意待在中國,但現在有小孩比較困難。可能有點矛盾的是,我還是會覺得用中文來創作是比較自由的,但是在東南亞有我喜歡的生活,就是比較輕鬆的狀態。所以那時候我覺得最理想的是我可以繼續在馬來西亞生活,然後在中國創作,但其實有點難,然後就慢慢懶散了。在生活上,我還是比較喜歡東南亞。
——您這幾年與馬來西亞的年輕電影工作者們有許多接觸,您覺得他們跟過去的自身經驗有什麼差異嗎?
其實我們也大概也就是十多年前而已,但那個時候沒有 Facebook 也沒有 Youtube。我們寄作品給影展的時候,還是用 VHS tape。一直到十年前,甚至在 2010 年以前,我們都還在寄 DVD,沒有 Vimeo 這種管道。然後我那時候拍片還是用Mini DV,所以我其實對現在的各種技術和他們可以得到的東西是相當妒忌的。但是他們不覺得,他們也沒有看到這種優勢,反而他們看的東西可能比我們還少,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做「SeaShorts」影展和「Cinephilia」(注6),真的是覺得因為他們上網可以看的東西太多,反而少看了很多,我們常會覺得如果你喜歡電影,為什麼不看一下這個?我們以前可能會很熱衷的買光碟,尤其是在馬來西亞有很多盜版碟,可以買到整套的金棕櫚、整套的各種導演,只要你知道自己要什麼,還是可以找得到。但是現在你會覺得他們不知道自己要看什麼,這可能是最大的分別,他們好像沒有看得太多,或他們看了很多不知道是什麼的,但當然還是有很多的例外,很優秀的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