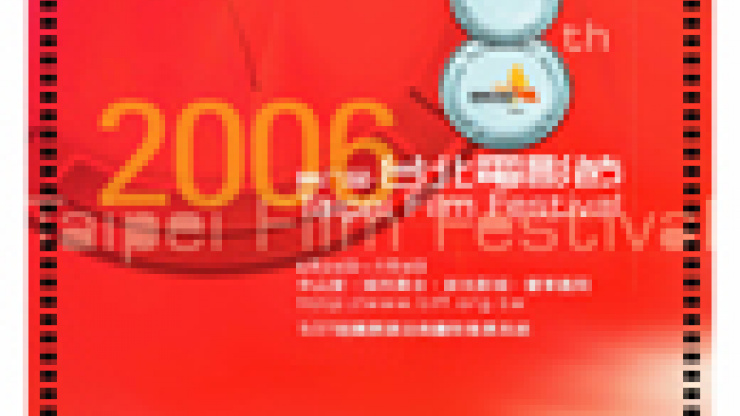「人生有夢、電影最美」──專訪《海巡尖兵》導演林書宇、《呼吸》導演何蔚庭與他們的攝影師Jake Pollock
誰說台灣電影圈不景氣,戲院內放台灣電影滿座率雖不是很高,但戲院外做電影夢的人可真不少,林書宇、何蔚庭和他們的攝影師Jake,秉持獨立精神,做電影夢不只用想的,還身體力行找機會學電影、拍電影。這三位電影工作者同《一年之初》的鄭有傑導演,有著拜把兄弟般的交情,互相力挺、彼此支援,他們共同認為在台灣這個資金不足、人力有限的環境下,惟有一起努力,才有機會打造一片天空。 有趣的是,何蔚庭和Jake這兩位從洋過海來到台灣的外國人,選擇台灣當作拍電影的基地,他們在此看到了希望,在無健全體制的台灣電影工業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和需求,Jake更有個外號叫包「板橋」,此乃意味著他其實是個完全融入台灣的外國佬,在尚未來到台灣之前,他崇拜台灣電影,進站之後、他實踐台灣電影。 所謂十年一覺電影夢,他們喊出了十年一「技」電影夢的口號,這幾位創作者謙虛的表示,他們的努力和進步的空間還很大,花十年的時間作為養成導演的訓練,是需要而且值得的。他們珍惜把握每次做電影的機會,在拍片中學習、組織團隊,在其中和自己的技術班底謀合切磋、建立默契,塑立自己的美學風格,尋求共同的理念,集體成就一部電影。 那一夜的訪談,聽這幾位年輕的創作者,侃侃而談他們的理想和遠見,在純真的笑容與耳語言說間,聽聞各自對未來的期待和對影像的堅持,愛電影像著了魔般,說起它,個個散發無比的光采在眉宇間,舉手投足間筆畫著框框(拍電影的視角)。或許他們知道,人生有夢、電影最美;在我看來,他們有夢,而且認真做夢。 小記:關於《海巡尖兵》和《呼吸》 《海巡尖兵》2000年3月18日,總統大選之夜,三名海巡兵一如往常的巡守宜蘭竹安的海岸線。上演著老兵欺負新兵的故事,黑夜的盡頭,傳說的瘋女人「兩八」出現,一兵趁機強逼二兵實踐竹安成年禮,那一夜發生了一些事,一切竟如此的無奈而荒謬的…。這故事所反應出的人性,不只是在阿兵哥之間的權力關係,更可引申到軍隊對人心的殘害,這也似乎對照著,社會中的現實生活,即有可能發生類似的權力關係與人性輪迴。 《呼吸》描述一個不遠的未來,流感病菌變本加厲,演化成以空氣為媒介的致命病毒。在這樣的世界裡,人人戴著口罩,一名高中女生心裡知道自己時間不多了,於是她選擇過一個屬於她自己的一天。在音樂的陪伴下,她和公車上的ㄧ位男生,發生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性關係。
可不可以先簡短的與觀眾介紹你們自己以及從事電影的工作和經歷。
林書宇:我是世新電影畢業,從小很愛看電影。因為小時候住美國,當時看了很多好萊塢電影商業片。而第一次會有念頭想要從事電影工作,是看完楊德昌所執導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所以特別有種親切感(當時張震演的就是我的年紀),雖然電影本身是敘述另一個年代的故事,但看了仍很有共鳴;那是我第一次希望這部電影不要結束,就這樣一直演下去吧,也是我第一次在看完電影後,認真去思考一部電影要如何做出來,並進而開始對電影幕後感到好奇。後來回到台灣(書宇的國小一年級到五年級在美國受教育),我家樓下有一家錄影帶店,我就常往那跑,有時,光是看錄影帶殼上的劇情簡介就可以看一整個下午,因常常去也就跟老闆熟了,到最後他常讓我拿回家看,看完馬上拿下來還都不收租金,就是在那個時候我看了非常非常多的電影,而且是什麼樣的類型都看。
高中的時候參加話劇社,有一次社團老師要我們演一個獨幕劇,但因為當時並不想採用老師發下的劇本,所以就自己寫《嗅覺》的原形,其實就是那個時候自己所寫的小獨幕劇劇本。後來大學考上世新電影系,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片《嗅覺》。(本片曾入圍當年金馬獎最佳短片)
因為有了一點小成績,就開始有些大頭症,認為電影不過就這麼一回事,後來出國深造,才發現電影其實不是自己想像的如此,原來自己是這麼渺小;在讀研究所仍不斷地創作,拍完畢業製作《跳傘小孩》之後就回台灣。因為想要更瞭解台灣的電影工業,我不能只是一味的作導演,於是就開始接副導演的工作,(曾當過鄭文堂、蔡明亮、鄭有傑……等導演的副導),也從中瞭解台灣電影工作是怎麼一回事,這些經驗讓我較有把握再擔任導演,《海巡尖兵》本片乃是歸國後,參與台灣電影圈的實務經驗後執導的作品。
何蔚庭:我是馬來西亞人,十八歲到國外唸書,先到多倫多念英文,再到洛杉磯,後來又到南加大接觸一些拍電影的東西(學生電影),之後又報考NYU(紐約大學),去了紐約五年,拍了短片,在當年NYU電影節拿了第三獎;畢業之後在紐約工作了兩三年(跟電影無關,一般的上班工作),這段期間有嘗試要再來拍個短片,但最後沒有剪輯完成。
2000年,我離開美國回到馬來西亞,看看有沒有發展的空間,接著又去了新加坡,給新加坡的廣告公司看了我所拍的短片,便開始接觸廣告,因為沒有很喜歡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環境,又因為在紐約很崇拜台灣電影,而且在台灣有親友,因此對台灣有種熟悉感,選擇來台灣發展。當時就用在新加坡所累積的作品集在台灣接了一些廣告,拍了幾年廣告當了廣告的副導,最後發現廣告並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就想不如再拍一部短片,就這樣完成了《呼吸》這部作品。
Jake:我是紐約大學電影系畢業的,跟何蔚庭算是同學。就攝影這部份,其實一開始並沒太大興趣,倒是高中時很喜歡演戲。原本是想作演員或導演,後來才發現自己在攝影方面比較有天分。很多人是上了大學才開始接觸藝術藝術電影,而我剛好相反,我是上大學之後才開始看好萊塢的商業電影。
能不能與觀眾分享一下,您們的拍片資金和現在台灣有哪些地方可以申請資金上,以及身為一個獨立製片導演如何與發行公司合作遞案的細節。
林書宇:拍片資金方面不是自己出就是申請短片輔導金,短片輔導金的好處就是它是一個很自由的基金,在創作方面出資單位不會有很大的干涉,不會因為要節省經費而被叼難,或是不斷地被要求解釋自己的創作理念。在花費的金額上,我的片子拍到現在做完拷貝大約一百二十萬,經費來源六十萬是短片輔導金,另外三十萬是自己存下來的錢,三十萬是跟別人借的,其中有十萬是鄭有傑借我的。(受訪者再次強調,並表示深切感激鄭導演的慷慨友情支援)
何蔚庭:因為我是外國人不能申請輔導金,因此直接不考慮這塊。所以我只能用我自己拍廣告所賺來的錢或另尋管道。其實這樣算是有好有壞,像我看香港的導演,他們也沒有政府的資金補助,但他們還是可以一再的拍片,對我來說在這方面我只要能找出一個訣竅,對以後拍片都非常有用,只是開始要下很多功夫,也會很辛苦,尤其在尋找資金,沒輔導金撐是很困難。《呼吸》的製作經費只有五十萬,連後來跑影展下來花了快七、八十萬。本片去年有在華納威秀放過兩個禮拜,現在也發行了DVD,我發DVD的做法是,在這部電影裡我有用到一個歌手的音樂,我就跟這個歌手的製片商量在發行影片時,你要不要也出一個單曲CD,於是我們就聯手合作,我想這是沒辦法中的辦法,畢竟沒有一個發行商會想要發行十五分鐘的電影。
何-何導演您的第一部創作即贏得坎城獎項,能否與讀者分享您那次的參展機會,以及在何種因緣際會下,會去投這獎項。註:本片贏得2005坎城影展國際影評人週「科達發現獎最佳短片」、「TV5青年評論獎」
何蔚庭:其實一開始沒有想太多要投哪個影展,當時因為拍廣告拍到覺得再這樣下去會迷失自己的方向,於是就決定要拍部短片。之前拍片都沒想過要報名坎城,都覺得應該投一些小影展就好了;片子剪好之後剛好到了坎城報名的截止日,就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將作品投出。當時為了報名坎城影展還特別將片長剪到坎城規定的十五分鐘,我當時的心態是既然決定要投影展就要投最高的,高的如果不中再往下走。那個時候JAKE幫了我很多忙在剪接這部份,甚至在送給坎城的DVD裡,有些聲音的mix都是他弄的。後來片子就這樣送進坎城,總的來說,這真的算是個意外。
您的電影在敘事上用了較新的邏輯和剪接與攝影,能否談談這部份創作的特質。(另也請攝影師Jake回答)關於風格的問題。 您的電影有受到日本電影或哪個導演的影響嗎?
何蔚庭:我所有拍短片的經驗裡通常有一個靈感都是一個畫面,我就常常將出現的畫面發展出一個故事。拍《呼吸》的時候因為擁有的資源和資金有限,所以就盡量在有限的資源裡把它做好。我對視覺的東西有一定的想法,我拍片的時候並沒有想到日本這一塊,反而是針對法國的一些導演,像Olivier Assayas和Claire Denis《Friday Night》,我們就以這兩個導演和他們所拍的片子的風格來討論,之後就開始拍跟人家借零頭片(零頭片指的是片廠裡用剩的底片)來拍,在拍攝過程中,發現可以用有趣的沖印技術,來統一不同零頭片的tone調,後來才知道這種沖印方式的可能性,在台灣還沒做過。我是一個很喜歡玩東西的人,既然沒做過就來試試看。關於影片的風格我想是因為製作限制的關係,像零頭片很短我不能拍太長的鏡頭,這樣動不動就要換片,有時候我剪接到最後會發現,我就只能剪接到一個程度,因為我沒有東西再剪了,於是整個片子的步調就會比較快。
而特寫的選擇,因我們塑造的是一個人人都戴口罩的的世界,如果拍到的路人是沒有戴口罩的話,這個世界就不成立,所以我就只能集中這兩個人(片中的主角),用特寫的方式處理。我覺得在風格這部分是製作環境促使你去這麼做,我在拍片之前有幾個比較Ok的視覺idea和幾部片子做參考,真正提到的東西都是直覺,我也沒有事先特定這個東西就是要這個樣子,於是整部片拍完之後,所呈現出來的風貌就是它的風格。
Jake:其實我們在拍這部片所使用的資源像零頭片這些,並不是因為我們偷懶,而是面對我們能用什麼,就要好好利用這些東西來塑出一個風格,在特寫這部分,也不是因為資金的原因,不能讓我們有大畫面(大遠景),因為我們都很愛Assayas (阿薩亞斯),他在拍法跟台灣電影是很不一樣的,國片很少人拍特寫,我們甚至討論為了給自己更多的挑戰,我們整部電影只用一顆鏡頭(85mm),因此這個決定讓這部電影更不像台灣“New-Wave”的風格。
林-《海巡尖兵》是您第三部作品,能否與觀眾談談這部份,以及在製作編劇短片的架構有哪些細節需要注意的。它的英文片名為the pain of others,為何想取這樣的片名。
林書宇:就像剛剛蔚庭所說的,你有那樣的限制你就只能那樣做,同樣的,我也給自己一個限制,讓我更須要細心的去拍不要浪費。至於當兵這題材,當然有部份來自於我服役兩年所看到的一些情景,再加以戲劇化,結構而成的劇本。至於片名的問題,源自於我讀了蘇珊‧桑塔格的一本書,<旁觀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書中所講的精神和正與我的東西有部份類似並有共鳴,於是就想用它後面the pain of others作為片名。
林-對於影片中低迷的氣氛和壓抑的氛圍,賦予很強大的節奏張力在故事中,您個人在這部份的設計有無具體想法?
林書宇:其實我拍完之後剪出來的東西差不多37、38分鐘,是有一個喘氣空間的,因為那時候想要報威尼斯影展,那時候威尼斯的限定是短片要在30分鐘之內,並且在拍之前就覺得這樣的主題不需要超過30分鐘,於是後來就把它剪成三十分鐘,導致在節奏方面我自己是稍嫌太快。其實剖開來看,從前面的鋪陳、中間的轉折到後面有高潮故事結束,我是用三幕劇這樣的方式在講這個故事,這也是這部片子跟觀眾共鳴最大的地方,觀眾看這樣的敘事邏輯是很習慣的。
獨立製片屬於非體制的影像創作,能否談談在這樣無具體實質支撐下,如何尋求專業的製作團隊,並有共同的理念完成作品,就統一的風格導演的要求,您們如何辦到的。
何蔚庭:我覺得在台灣拍片,如果有製片公司出資的話,他們不可能有自己的班底,到最後還是得找外面的人,我今天會選擇在台灣先拍短片再拍長片,是因為我要用短片先測試一下,知道整個製作環境是怎麼一個樣子,我才敢拍長片,所以在拍短片的過程中,我還是得找到我們能配合的班底,除了Jake之外,自己還是需要慢慢的組成了一個team,有些是利用拍廣告的經驗,有些沒辦法一定要另外找一些人進來,像杜篤之,我之前沒有跟他合作過,我經過短片這個東西,學到怎麼跟他合作,學到杜比音響怎麼操作,如果我未來有拍長片的機會,我想是很重要的一個東西。我覺得短片如果能在一個比較有限制的情況去拍的話,是一個很好的訓練,對我來說以後拍長片還是可以用一樣的模式去拍。
在台灣拍片都是很獨立製作,沒有所謂集資的東西,所以這算是很普遍的現象。我覺得導演跟自己的team應該是要共同成長。所以我組team的過程中會希望大家一起成長,《呼吸》這部片會有一點成績,很大的原因是因為我們(這個團隊)之前就有一起工作過兩次的經驗。
林書宇:在班底方面我的問題沒那麼大,因為做了很多次的副導,認識了很多人,不管是技術人員還是演員,在拍片現場導演會花比較多時間跟演員在一起,但我做副導是花比較多時間跟工作人員在一起,很容易跟他們培養感情產生默契,當我做導演時,當然就再找這些人來工作;演員也是一樣,像我認識有傑很久了,就覺得有傑可以演就找他來演。這部份可以建議學生拍片時,你不要以為去找一個像李屏賓師傅這樣大師級的人來參與,拍出來的片就可以像侯孝賢導演,最好的狀況是找你一群好朋友,大家一起打拚、一起成長,這是我從個人經驗後的感想。我自己也從中成長學習不少。
J-您在攝影部分,維持一定水準的技術和影片調性,能否與讀者分享,在和鄭有傑、林書宇、何蔚庭這三位導演工作時的溝通協調。而您有無自我個人的堅持和影像風格在每部影片當中,如果有的話又是什麼。
Jake:因為每個導演都有不同的故事要說,技術人員也是一樣,像我在攝影方面對於很多不同的東西我都有不同的反應,像《呼吸》、《海巡尖兵》和《一年之初》這三部片有各自所走的路線,但是每一條路我都有一些話要講出來,在《呼吸》中我有得到一些經驗,可以利用在《海巡尖兵》裡,也可以學到不同的東西,之後又接到《一年之初》,又嘗試了一些不同的東西,,這是我希望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
而當初在拍這三部片時預算就不夠,下一部電影的預算又會不夠,在預算不夠的情況之下你還是得做出好東西,因為觀眾進戲院不會管你幕後所面臨的問題,他只管那個故事好不好看,如果你沒辦法付起這個責任,那你就不要做。我們在拍這三部戲時,都在資金不足的情況下想辦法讓出來的東西剛好,我們沒有那種東西做不好就算了的心態,在時間和預算把關的很緊,看我們可以做到怎樣程度的好東西,讓觀眾看了很震撼。
我覺得預算的多少一定會影響影片的風格走向;之前在美國拍片,如果錢不夠做不到就算了,但來到台灣之後就不會這麼想,就一定要做到最新的東西,所以很多時候我讓製片很頭痛,但我希望這問題寧可讓製片去頭痛,而不讓觀眾頭痛,這樣出來的片子才有機會成功。
據說兩位導演都是具有一些西方教育背景的創作人才,能否談談這部份的文化衝擊對你們在創作和題材與工作上,有無影響,如果有的話是什麼。
林書宇:當然是有影響。2002年我在美國畢業(拿到碩士學位)之後學校有給一年的實習機會,但我選擇回來台灣,因為在台灣才有我想拍的題材,所以我所拍出來的東西台味很濃厚,甚至當時在美國所拍的小留學生,也是在說台灣人在當地的故事,我所關切的還是台灣的文化、這塊土地上的人事物。西方的文化幫助我的是一個敘述方式,畢竟國外的電影走了那麼多年,方式那麼多,受到那些影響是很直接的,我自然而然會覺得一部電影要好看在於要如何去敘述,每一個故事適合的方式不一樣,所以我並不執著於一個既定的風格,就像看過我所拍的《海巡尖兵》的人就會很難與我上一個片子做聯想,也不會猜到是同一位導演所拍;雖然我沒有既定風格,但我會依故事的類型安排最適合它的方式,拍出最能令觀眾感同身受的創作。
何蔚庭:我覺得在美國訓練的好處,是會讓你對於拍片的整個過程有比較深的了解,像我們知道拍片的限制就會做很充足的準備,這些東西就是在美國學來的。我在美國拍一些學生片,也是用工業電影形式的手法來完成,這一套當時在美國所學到的,事前的準備工作都要做的很足,不會說到了現場才說要憑感覺、鬆散的那種態度。第二件事情就像林書宇說的敘述的方式,在國外是被訓練要怎麼把故事說好,當你懂得如何把故事說好,要拍什麼樣的電影類型都沒問題,相較於台灣的導演只善於一種說故事的形式。我們的優勢是我們有一個說故事的訓練,在美國這一方面的訓練是很重要的,也因為在美國所學習到的這些背景和生活方式,讓我們回來台灣拍片在這方面的優勢比較強。
還有一方面是由於我是馬來西亞人,不管在美國或是台灣我都是一個外國人,因此我會習慣用一個外國人的角度去看我所住的那個地方,即使我沒有受過美國的訓練,在台灣拍片我還是會用一個外國人的角度來看,這方面又會使我在拍片時跟台灣人自己說故事有很不一樣的觀點。
Jake:我覺得像兩位導演對不同文化的了解這麼深的好處,是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在台灣要用什麼樣的方式說故事,而不會去想一些像情境喜劇這類型,不適合台灣文化的模式去拍片。在台灣拍片的預算跟美國其實差距是非常大的,在台灣拍片的預算可能一千五百萬~一千七百萬不等,相當於不到美金五十萬,這樣的預算在美國拍片根本拍不到什麼東西,可能還得省去底片的錢改用DV,而且工作人員都還得找朋友充當,監製可能還需要好幾個人,而且大家各有分歧的意見。
在台灣雖受限於預算的空間不夠大,但拍起片來起碼還是可以拍六個禮拜,在美國要用這樣的預算拍片,頂多只能撐兩個禮拜,在同樣的限制上的做法就有所不同,因為我在美國和台灣都有拍片的經驗,所以我會思考在台灣拍片的好處在哪裡。在台灣拍片通常監製都是只有一兩個,而且很重視導演的想法,這方面在美國是根本沒有,在台灣給導演發揮的空間相對大很多。
能不能就您們實際的工作參與台灣電影拍片的經驗,談談台灣電影工業目前的狀況,以及如果有對電影充滿夢想的年輕人,有什麼建議呢。
Jake:其實每個人都會找到自己的做法,像我們剛開始拍片的時候,網路、手機都還沒有拍東西的功能,我覺得現在會想辦法利用新科技來爭取機會的人,才真的會比較有機會。另外,其實不管你決定要做什麼,導演、編劇、攝影師都好,起碼都要花十年以上的時間累積,在這段時間內才能得到寶貴的經驗,影響之後的功力;一開始會覺得十年很長,會等不及,但當你過了這十年你會覺得其實時間過得很快,到現在我拍過5部長片和20多部短片,差不多在這十年逐漸累積的。
何蔚庭:我覺得新人開始不要太急,尤其當你的社會經驗不夠,拍什麼好像都會不對,所以新人其實不要動不動就想拍長片。雖然短片是最沒有商業市場,但短片是一個最能讓你學習的東西,頂多就是拍壞了不要,但它是可以讓你一直走下去的,不像長片,動輒就兩千萬,如果少了短片的訓練,一下給你兩千萬你也不敢馬上接手就拍。另外,我有很多的經驗是從廣告學來的,雖然廣告可能是很商業性的一個東西,但其實我今天拍得出《呼吸》是因為我在廣告界訓練過,廣告的好處是它給你限制,你就是要在30秒內拍出一個作品,因為是別人出的錢,預算也是有限,要在這麼刻薄的限制下拍出一個作品其實也是一種訓練;所以我建議新人可以嘗試去拍一些廣告、拍短片,等時間、經驗成熟之後再拍長片。
林書宇:我覺得不要一直急著找機會,卻不顧自己的基本功有沒有紮實,像蔚庭的基本功是從廣告學來的,而我的基本功是做副導的時候所累積,因為做副導的時候可以讓我知道當導演要求不合理時工作人員的痛苦和無奈,所以自己當導演,就會注意到這些東西,畢竟拍電影是一整個團體的事情。我一直認為既然找了這些專業的人合作,如果每個人都能拿出自己百分之百的實力來做,那這部片絕對會更好看、更成功。
而要如何讓他們付出百分之百,這些都是要從基本功來的。也就是說不必一開始就急著做導演,重要的是到底準備好了沒。我相信現在拿著三千萬給任何一個電影系的學生叫他拍出一部長片,他一定馬上答應,因為要抓住得來不易的機會,但真正問題在後面馬上就出現了,要怎麼運用資金,要怎麼跟演員溝通,要怎麼跟攝影師溝通,要如何跟工作人員正確的傳達出導演要的方向,如果請到一個大牌演員,你有沒有跟大牌演員合作過的經驗,要怎麼跟大牌演員安排時間,如果遇到大牌演員耍脾氣時,該怎麼處理要怎麼溝通等等,這些狀況絕對不該在拍第一部劇情長片時發生,也許有人會覺得第一次失敗,學了個教訓也好,但這風險太大了。因為當你賠了第一部大片對之後的影響會很大,像要找投資人或贊助商之類的都會變得很困難,而且很難翻身。
三位能否與觀眾聊聊最新的計畫,有無拍長片的計畫呢? 謝謝您的建議和回答,祝一切順利。
何蔚庭:下一部片還不確定是長片還是短片,我不會因為拍完了短片就要拍長片,一切都要視資金來做決定。
林書宇:接下來會嘗試和一個編劇合作,寫一個關於關於一個高中時期的成長故事,述一段純真年代結束的故事。部分半自傳。現在我腦袋裡已經有片子的雛型,其實跟一般別人所拍的青春校園的電影是很不同的。希望有機會能夠找到資金完成這部片,這是目前在計畫的電影。(歡迎投資者與林書宇連絡)
Jake:我今年秋天要幫鴻鴻拍一部電影,這應該是我下一步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