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作為一種迴返,或是重新出發——記 non-syntax 實驗影像展
以語言學領域來說,構成句子(sentence)的語義(semantic)與語法(syntax),以及由字母(alphabet)組成之單詞(word),幾乎成為語言的基本單位。此一「語法」及「語義」亦存於語言學外,視論述場域及語境被抽換成各種詞面。以電影為例,在論及敘事、類型(genre)、文本等範疇時,電影語言理論(linguistic film theory)曾針對其進行諸多論述。而若是檢視千禧年以降強納森.柯拉瑞(Jonathan Crary)、諾曼.艾考特(Noam M. Elcott)等視覺史學者進行之的媒介考古學,亦能順其思考路徑,梳理出數種重構電影機制/語彙,並重新考慮原先看似線性、由製作、發行、展示、觀賞等機制(institution)(注1)部署而成之「論述」的嶄新詮釋方法。
諸此理論建構於干擾固定句構、否定定型論述,並以殊異的語法重探、重組、重構「電影」及其可能的嘗試手段,亦能在 2022 年於台北 ROOF LIGHT 舉辦的 non-syntax 實驗影像展(non-syntax Experimental Image Festival,下簡稱 non-syntax)瞥見。該影展敞開黑盒子式的典型電影想像,將「電影」(cinema / film / picture / image)擴延至多義語境中,視「電影」一詞為懸置的問題,並在策展與觀影的實踐中試圖接近問題本身。本文圍繞於 non-syntax 的策展實踐,邀請策展人許鈞宜、金秋雨和客座策展人許耀文一同討論 non-syntax 意欲展開之問題意識,並結合筆者自身觀察,論述其鬆動「句構」之意圖,以及想像「電影」的另類可能(注2)。

非後而非
「讓我們下去,在那裡打亂他們的語言,讓他們不能知曉別人的意思。」—— 創世紀 11:7
巴別塔的故事啟示人類擁有數種語言的起源,並警吿人類,傲慢終將招致自我毀滅。聖經中,耶和華欲透過「多語」分化人類,卻沒意識到其於降下「天罰」的同時,亦開展了以語言系統為底,構築多樣文化系統的基礎。若將這則故事置於「電影」(cinema)的範疇中,事實上,七〇年代擴延電影(expand cinema)的出現(注3)已揭示此一媒介之邊界已不再穩固。究竟什麼是「電影」?「電影」有什麼樣的可能性?諸此問題的出現及圍繞此問題的論述/創作嘗試,皆已捨棄恪守媒材殊異性(medium specifity)的現代主義式思維。同時,當「電影」離開傳統意義上的「電影院」,進入到美術館、藝廊等白盒子後,其再次從根本上鬆動了「電影」一詞的定義。然而,與其說此股新浪潮是電影領域的嶄新嘗試,毋寧說這是對此媒介的一次歷史迴返:「電影-戲院」式空間部署實際上並未存於二〇年代之前,早期的電影大多流轉於咖啡廳、廣場等場域放映,而非如今人們熟悉的黑盒子。擴延電影的出現,最大的意義不只在於產生諸多全新的放映/創作形式;同時,其對傳統電影語彙(lexis)之鬆動,及伴隨鬆動而敞開的「想像的可能性」,恰是擴延電影之於整體電影創作與理論的最大貢獻。
此種「想像的可能性」,亦是 non-syntax 的基本姿態,許鈞宜分享,作為策展論述的核心概念,取消電影既有的語法與結構,實際上並不是單純地強調電影(cinema)機制、歷史及特定類型層面上的徹底消失,也非單純以流動影像(moving image)指稱當代影像創作中去疆界(deterritorialization)、跨領域的迥異實踐;相反,non-syntax 試圖在揭露、逾越電影既定語法的同時,亦提取屬於電影自身特有的問題。所謂「電影自身特有的問題」,看似又繞回電影性(cinematic)或巴贊為人所知的那句「電影是什麼?」欲探究之本體論(ontology)問題,同時,亦如許鈞宜指出,在揀選本次影像展作品的過程中,始終緊繫在「電影是什麼」以及「電影將是什麼」兩個問題;然而,拋出這樣的提問並非意味 non-syntax 將順著前人梳理之路徑前行或為這些問題提供一個固定的新解答。反之,彰顯此二問題意在啟動前述之擴延電影式的想像原動力,「上述問題亦曾分別於影史不同時期被提出,前者總是意味著電影仍具潛能、有待開發其特質的時代,而後者則面對電影自身已消耗殆盡、被迫轉至他處的情況,這兩個問題在展覽中,將成為擴延與凝聚的二重運動。」
不過,此種說法,及並存於影像展名稱及策展論述中的那句「取消自身語法」將面臨另個問題:若説「取消」作為反對既有定義的基本態度,那伴隨而來的便是隨「取消」後馬上迎來之「懸置」或「空缺」意義的追問。亦即,如果電影「不是」前人定義的「什麼」(what),那它將生成何貌、往何處去?然而,如同前述,為上述問題提出全新解答並非 non-syntax 的目的;許鈞宜與金秋雨更視這些問題為啟動思考的原初動能:「關於如何『取消自身語法』,對我們來說是永遠不會有明確答案的。它最多只能是一個摸索的『過程』,而非直達終點之『答案』。但是,如果沒有人實際去行走這條看似沒有解答的小路,那麼『語法』和『框架』將會逐漸根深蒂固。」金秋雨強調,「取消」並非永遠意味著「創建」,「我們最常被誤解的是『想找到一個新的文脈』,或是想創建一個新的『定義』,而這恰恰與我們的初衷相反。 non-syntax 的策劃其實是想質問典型電影建構機制中已設定完成的固定視角,並希望藉由『提出質問』來『取消』,而非有些蓋棺論定地在此基礎上『重構』一個同樣僵化的新視角。亦即,我們不希望再有『後』(post)出現,只需有『非』(non)就足夠了。」

此種「探索」而非「解答」的姿態,便是前述之「動能」與讓人摸不著頭緒的「想像原動力」。許鈞宜接著說:「取消自身語法亦是重新創造語言的時刻,在擴張與聚集間,我們試圖深化著屬於電影的(cinematic)問題。」此一深化之意圖於篩片階段已然生成,並且,在該階段觀看作品時策展人便開始想像這些影像的可能性。許鈞宜列舉本次放映作品的特色:「諸如某些作品藉由純粹的閃光或者靜態圖像的高速拼接,一再地令觀眾意識到構成電影的根本條件;或者揭示電影作為群體記憶、載寫歷史的重要媒介。另一方面,電影則又成為了解析物質、重構檔案的介面,藉由投映(projection)的形式,觀眾將在這邊意識到電影的另類可能。同時,亦有如部分參展的作品,是為多頻道、影像裝置的變奏版本,其也將令觀眾感受到影像原先與建築、觀眾性、空間的關係。」
移置與互文
在這個充滿「非」(non)的影像展中,還有另個需要釐清的問題,即為何在中英名稱上 non-syntax 皆使用了「影像展」(image festival)而非過去較常見的「影展」(film festival),並進一步在「影像展」前綴「實驗」一詞?許鈞宜解釋:「對『實驗影像』一詞的使用,是當初在創立這個計畫時,便試圖以某種模糊性——無論是歷史中各種實踐的錯雜發展、或在當今論述在同義/多義的語境中——去強化影像本身的多樣性。」此點亦奠定了策展時挑選作品及規劃子題的想像,有趣的是,於策劃階段時策展人並未先行設定出數個固定的子題,並將作品置入這個已成形的穩固框架;相反,所有子題的誕生,是在策展人檢閱作品時,考慮作品與作品間的關係,試圖從中逐漸描繪出清晰的輪廓。「在作品的選擇間,我們試圖點出影像難以歸結在單一網絡下的狀態,諸如有些作品透過物質性的思考與電影(film)對話、又或者是在純粹的聲光表現更加接近流動影像(moving image)的存在等,甚至是本次結合攝影與擴增實境的裝置作品,都想要讓影像在分類與認識上產生不確定性。」
亦即,non-syntax 的「非」,並不是單靠場地與播放方式等放映性(projection)因素實踐(即便這亦為一種有效方法);此精神早已自影像展尚還只是個「念頭」時便已成形,並隨計畫的完備逐成一種態度。許鈞宜分享,抽換該詞(實驗影像展/影展),是希望能將實驗作為動詞,令觀眾意識到對類型的不設限、以及作品是如何各自去進行對影像的「實驗」。同時,也試圖在各單元的策劃下,逐漸讓觀眾意識到電影發明至今不斷變化、延伸的系譜。

另外,雖在既有的各種影展活動中,放映「場域」的移置(relocation)已非新鮮事,但選擇原為攝影棚的空間舉辦影像展亦是其實踐「非」的其中一環。許鈞宜回憶道:「在兩年間(注4)的展出經驗中,當初似乎直覺地選擇了一種開放、流動的方式展覽,這可能源自於個人的觀影經驗,無論是在電影院或美術館,好像總是有著意外進入某一空間目擊影像於眼前展開的時刻,我們便嘗試留存著這一個瞬間,希望能直接地讓影像與場域就地形成密不可分的狀態。」此種重新連結影像與場域,甚至進一步將觀眾納入整體放映空間的觀點,與 non-syntax 的子題也產生了互文,「我們期待著觀眾能直接地與影像相互遭遇,讓影像在身體的變化,如移動、分心、停駐等落差之間持續生成。因此,與其說展覽整體是由策展人彙編而成的複合文本,倒不如說是由整個空間、觀眾所共構的場域。」
以此延伸,若檢視影像展子單元,亦能瞥見策展人試圖共構空間與影像,使觀眾能夠超越被動接收的單線觀影模式,並讓視覺(visual)外的身體感知(perception)也成為觀影經驗的一部份。許鈞宜指出,今年更早前策劃的單元「移行風景」中,即找尋了如同風景般流動的影像,同時在展覽空間規劃上,試圖讓觀眾在屏風、窗面與小徑間任意的移動。「因此,在放映——或說使影像顯現的思考上,展覽嘗試透過作品的展出,令觀眾意識到過往由電影所開啟的觀看脈絡、物質條件,以及影像與身體感知的聯繫。」
時間與記憶的後像
前述對視覺外之身體感知的關注,亦能於其他策展子題中瞥見,其中,「記憶暫留」可以被視為展開後續涉及認知、記憶等母題的起點。該子題以後像(afterimage)為母題,試圖藉此將影像展的討論延伸至記憶與影像間的關聯。在此,後像既承繼了十九世紀以降視覺生理學(physiology of vision)之嶄新發現(注5),到電影(及前電影)視覺機制的發展脈絡,亦藉此媒介史將問題推展至前衛、實驗電影之討論。許鈞宜表示,這個單元的構想,剛開始其實是想安排一個聚焦將過去前衛主義、經典實驗電影手法延伸至當代創作實踐的單元。然而,這使他開始爬梳實驗電影特別著重之「手法」或「技術」的流變,以及,探問究竟什麼樣的特徵能成為定義「實驗電影」的核心等問題。「當時自己腦中好像總有模糊的情景,像是光影閃現又消逝,或是在瞬間開始與結束的顯影。突然,我意識到在不同年代的實驗電影發展中,皆關注著影像如何在場、顯露之問題。無論是從蒙太奇在影格間製造的衝突(如愛森斯坦、維托夫等蘇聯導演)、來到光影的激烈閃爍(像是美國導演 Stan Brakhage, Tony Conard,抑或日本的松本俊夫),以及在可見性持續缺席下所形成的影像(諸如莒哈絲電影中聲畫分離的狀態,或是賈曼對影像的抹除/創造),這些作品好像都嘗試去體現出肉眼不可直接感受的影像為何。」

許鈞宜接著說道,「於是,回到構成電影的根本機制,亦即由速度所造成的視覺暫留,『記憶暫留』便嘗試專注於『後像』在不同時態中的顯現狀態。」這裡指涉的時態,並非單純的歷時性(diachrony)時間,而是牽涉創作者、作品、放映狀態、觀者等相互交纏,最終於放映場域中出現的共時狀態。「在作品的組合間,一方面後像指涉著在感知生理的間歇刺激間所相互交融出的產物。我們將不再能用固有『語法』的結構將影像視作由 A,B,C 等單元組成的序列,而是在閃滅間存在的中介狀態。另一方面,後像某種程度上更意味著『影像之外』,其總在銀幕與視網膜以外之處不自主地成像。如同澎葉生的《在馬祖,她一無所聞。她聽聞一切。》(She heard nothing in Matsu. She heard everything.,2021),便在黑幕的大量出現中,以聽覺建構出一處不可見的聲景(soundscape)。」同時,後像更抽象的意味著生活、情感在發生後褪去、質變的過程,「影像在此不再是指涉某一片刻的精準索引,或保存事物樣貌的工具,而是日常、記憶與歷史無可預測的變化過程。後像在此已無關正負、虛實,儘管不由肉眼所見,但它無疑是影像自身的一部分。」
遞迴/循環的念頭
「從『記憶暫留』中展出的作品《博覽會電影(它是我的記憶)》(Expo Film (this film is my memory),2020)裡探討膠卷與記憶之對話,到『迴聲』單元裡的《遺忘之室》(A Room of Oblivion,2019),以記憶卡中的未刪除的數位檔案,反思著情感消逝等問題,皆可見影像與我們極為複雜的交錯狀態。」
若從循環播送(iteration)此一放映手段考慮策展子題,亦能發現其解放了過去針對單部作品,或以此為單位形構檢視策展規劃的思考路徑。然其取而代之的是,解散壁壘分明的「單位」後能夠讓觀者自由介入/定義的開放動態。此種動態回應了圍繞在「記憶暫留」、「模糊的冥想」以及「迴聲」三大單元中的聯覺性身體感知問題,並再一次取消典型論述中作品、影展及觀者間的分立距離。金秋雨首先迴返影像史,指出影像與記憶的循環關係:「與我而言,整個影像史就是一部記憶史,一切都是圍繞各種記憶生成的。記憶包含了時間,一旦成為記憶的瞬間,就會以各種方式、方法以及型態循環。」此種循環成為策展的起點之一,許鈞宜接著說:「在『記憶暫留』與『模糊的冥想』中,我們想挑戰幾乎抽離敘事跟語言的情境,於是相較於另外兩個單元,它們更接近純粹的聲光展現。也因此,在流動、無場次區隔的放映方式(也就是循環放映)下,觀眾將在其中感受到光線、顏色、運動的顯現。甚或,感知的變化將徹底先於觀眾對作品資訊的理解,像是在某一作品放映時、仍持留著另一作品於腦中的餘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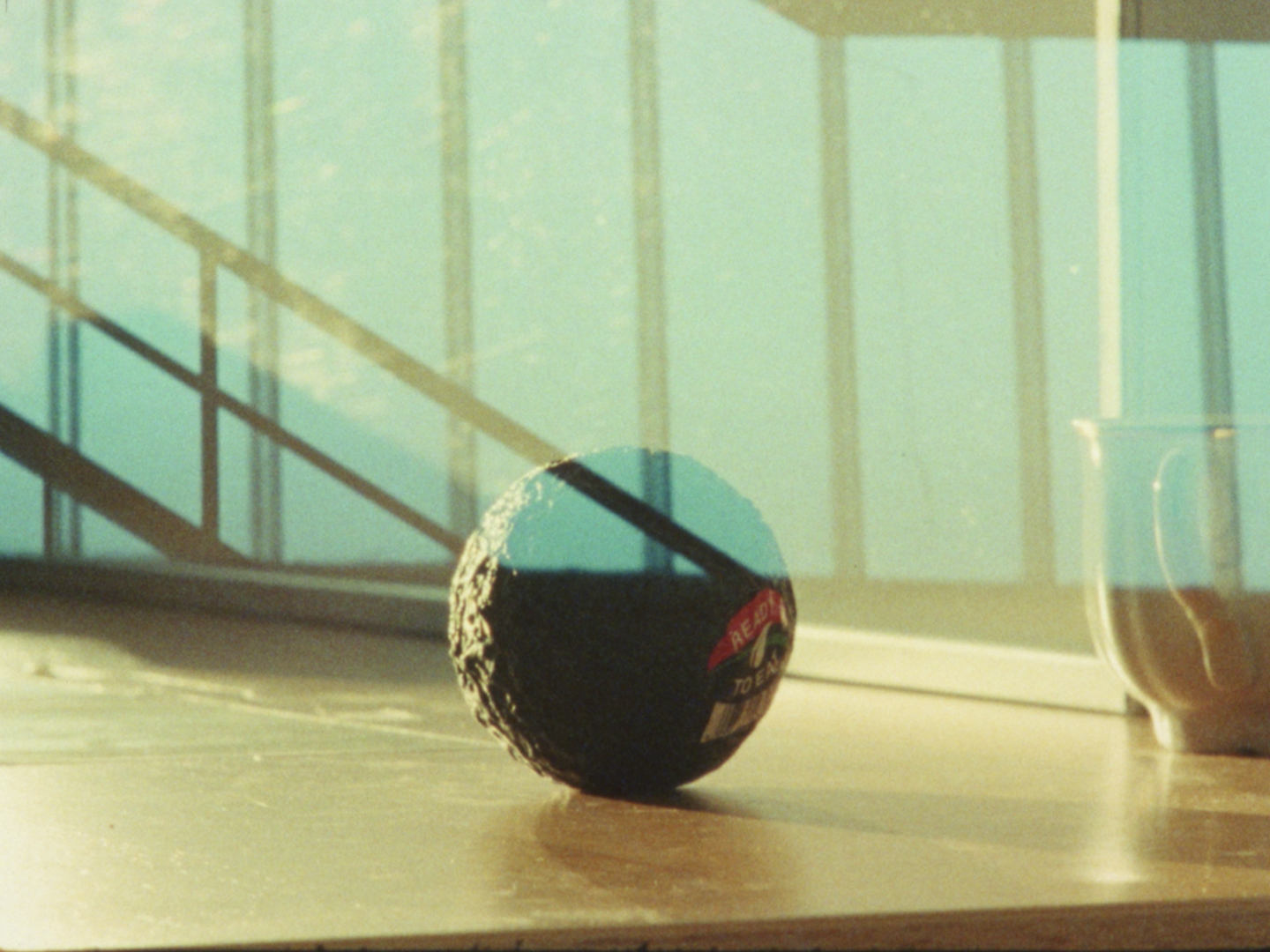
除了以影像與記憶為切入點外,許耀文試圖從國際疫情所導致的全新人地關係,並揉合自身閱讀經驗,在「迴聲」中描繪一條空間-身體-感知的策展路徑。「這個單元是從我過去關注的主題發展而來,除了去年(2021)協同策劃英國緩慢影展(Slow Film Festival)線上專題「島嶼」所產生的有機對話狀態(注6)外,也和我今年的閱讀經驗有關。」許耀文提及,他受近期閱讀讀物《地景》(Landscape,2021)和《空間物種》(Espèces d’espaces,2019)啟發,其所開啟之空間/地景想像,成為策展時回應疫情時代的身體-空間、意識-空間狀態的出發點。「我希望將自身在疫年時代思索和斷絕已久的外部世界之間的距離,和因時光沈澱逐而萃出的個人情感與記憶置入策展中,希冀觀眾能在觀賞過程中找到共鳴,聽見來自彼端的迴響。」
影像-創作-物
「記憶暫留」、「模糊的冥想」以及「迴聲」聚焦身體、記憶與空間三者不同的共構關係,然而,記憶不只是身體性的,亦是技術性的問題。此一問題將目光轉至所有「留存記憶的技術」——書寫、攝影、音像⋯⋯等——的討論,並進一步重構了人類對物、事件、他者等可以概括成「世界」的認識論。換言之,究竟技術與物/歷史/時間的關係是什麼?以及,這些關乎記憶/錄的技術又如何構成人類理解事物的方法或取徑?在「空間的物誌學」與「測量、邊界、虛構」兩大單元中,觀眾皆能瞥見策展方看似弔詭地,一方面在這個由複製技術(影像)所構成的展覽中,試圖將「物」的發言權還給物自身、繞過與「人」密切相關之技術,盡可能創造「無人」的,由物開顯自身狀態;一方面也意圖重構人對某物、某地的認識論,並將「影像」或「影像創作」視為一種重新認識事物的可能或方法。潛於這些論述中有些矛盾的存有問題,以及前述之未解疑問,不免讓觀眾感到有些不安,許鈞宜解釋:「『空間的物誌學』或許在命題上,會令人想到當代興起的物導向存有學論述;但實際上,此一主題的構想卻來自歷史中極為實際的視覺技術。」許氏以攝影為例,指出其歷史發展中對特定拍攝題材的轉向:「在攝影術發明不久後,比起以鏡頭凝視人類面容,攝影更為執著在對物的紀錄上,無論是類型學式對物種的視覺建檔,或是藉由望遠、鳥瞰的機器視覺觀察著自然地貌,或是透過顯微攝影或者特殊顯影技法,使得物質內的結晶或所散發之波長變得可見。」
透過攝影的例子,許鈞宜意欲表達的是影像史與「物的認識論」之間的緊密關聯:「可以說,影像史的發展必然離不開人對於物種的認識。然而,在此單元展出的作品中,影像雖然如實地呈現出物質的細部,但在此卻產生出某種不確定性,『物誌學』(topography)看似是對物質的註記跟載寫,實際上卻更像是以虛構開展的書寫。在此物質不再是被人類所解釋、說明的對象,而是成為了回視歷史、想像未來的基礎。」將目光從人類及(由人類所發明的)技術轉向物件本身,實際上昭示了創作觀點上的根本轉向,「比起我們所熟悉的、由作者話語建立的批判陳述,這邊更多的是從物質/物件出發的思考。影像創作在此並不是主觀地將個人思維植入物體,而是引出物與存有的存在關係。」許氏進一步以單元中的作品為例,指出其開創之可能性:「如同蘇郁心《Blast Furnace No.2》(2022)討論的煤礦、林勇氣《細胞與玻璃》(Cells and Glass,2020)的玻璃礦物、史文華《凝結物:波士頓市政廳》(Concrete: Boston City Hall,2021)的水泥與建築,或是陳君典《蜃樓記》(Chronicle of Nowhere,2022)對建築廢料的關注等,當觀眾看見岩石的紋理、媒材表面、抑或由物質所構造的文明遺址時,將逐漸越出人類存有的範疇而轉往物的視角。」藉此,「我們將可能另類地思考時間、歷史與存有等問題。」
「測量、邊界、虛構」則更進一步深化影像與「重建對某物的認識」間的關聯,試圖質問觀察者與被觀察物之間既有的主客關係。許鈞宜表示,「在該單元的構思中,更想討論的是看似略有差異,表述影像創作者、導演、拍攝者、觀察者等多重身份的詞彙中,實際上共享『持攝影機觀看』的行為本身。單元中,各個作品不約而同地企圖扭轉觀看者的身分與位置,帶著攝影機踏查各種空間,即是對原先被檔案紀錄的內容提出質疑,試圖以身體直接去經驗此些場所與地點。」也就是說,物與觀察者、技術與身體,在此皆非二元對立的光譜兩極。相對,創作者的實踐及其被彙集成單元之策展論述,皆意圖轉譯(translation)典型論述中的純化(purification)傾向。「因此,這個單元中的作品皆格外關注身體之在場以及創作者與檔案的關係。同時,『重建對某物的認識』一方面被作品體現為對於事件現場的迴返與遊走,另一方面則更為後設的以重組檔案內容,擬造出對未知空間的探索、或對未明歷史的爬梳。」

若是檢視該單元作品,亦能發現創作者意圖干擾上述固定論述之嘗試,許鈞宜舉例:「像是查納松.柴奇蒂波恩(Chanasorn Chaikitiporn)的《目盲之光》(Blinded by the Light,2021)便透過泰國電影資料館的視聽檔案,在蒙太奇間揭露出泰國電影的出現,實際上離不開西方殖民勢力進入此一歷史語境;或是莉莎.麥卡提(Lisa McCarty)的作品《Seeing Spacecraft Earth》(2021)則揉合造假的視覺構成及真實紀錄的音訊內容,拼湊出登陸月球的過程,混淆著歷史與科學對於太空的認識。」
迴返,或是重新出發
綜覽 non-syntax,不論是策展論述或實際進入放映空間,皆能發現其意欲將觀眾置於不穩定的觀看位置。然而,此種不穩定,恰是其使用「否定」——或者如影像展名稱所述——將「非」作為展開對記憶、空間、歷史、影像等母題之探問的基本姿態。影像展以一系列的提問質疑典型論述(discourse)時,亦同時將觀眾推至既有認知的邊界,使每一次的觀看,以及於放映空間中的游移與渡步,成為重新出發的原動力。不過,「非」看似只彰顯其「破壞」姿態,或者隱約透露擾動既有結構、延異至沒有盡頭之「終點」的態度,其不免被誤解為一種相對或虛無主義。但,在這個發生於放映空間的「分析工程」(注7)中,non-syntax 實際上也給出了一個在「非」之後的「可能」:透過迴返歷史的原初起點,從中錯位出懸殊(suspend),以此探詢「多重」(而非強調追尋「本源」式的「單一」),重新展開觀者考慮影像的旅程。
以「否定/非」(non)為引,non-syntax 在敞開觀眾對電影的想像時,亦點出了「否定」一詞的潛力/義。在此,否定作為一種迴返,或是「重新出發」,使潛藏拉力動能之「迴返」與富含推力動態之「出發」產生碰撞,以發現取代化解,以擾動取代穩定,於二力矛盾間,尋找動態且不息的意義蹤跡。
又或者,也許可以想像,此時我們正身在一輛說著「一種以上語言」的馬車上,背著巴別塔的廢墟,長往遠引⋯⋯■
.封面照片:《記憶擴延》作品照片;2022 non-syntax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