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饒的意義之海──《少年Pi的奇幻漂流》
《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不是印度男孩版的《浩劫重生》(Cast Away,2002),猛虎理查帕克也並非足球威爾森的替換友伴,這場驚險海難後的餘生漂流記的要旨,更不在於讓觀眾「見證」英雄歷劫生還的不凡、相信眼前的一景一物,它反而訴求於打破直觀表相,透過敘事框架的驚人反轉,進而思考複雜而多義的生命本質。
在視覺上,本片驚心動魄的海難、栩栩如生的猛獸、幻夢般的瑰麗奇景、劃時代的3D感官體驗在片商鋪天蓋地的宣傳造勢下,成了必看的重點。但觀眾若期待被「衝出銀幕」的老虎嚇到,恐怕會有些失望,3D對於李安而言是表現文本肌理的戲劇語言,而非操弄風格的炫技工具,有別於諸多商業娛樂大片,《少年Pi》的3D影像並不誇大物理空間,或玩弄迎面衝向觀眾的縱深運動,以片中主角經歷的兩場暴風雨為例,前者是生命遭逢驟變的傷逝,後者則是絕境中對冥冥中未知力量的深切質問,兩場都蘊涵了巨大的情感張力,3D攝影在洶湧海浪中注入了厚實的密度與水體觸感,讓人徹底融入於寫實的情境,而非被突出、外放的3D視覺分散焦點。本片3D的優越成果,也展現在另一個Pi於海面漂浮時的觀點鏡頭,它同時涵納水下/水上/天空的遠近層次,形成極為寬廣、包容的視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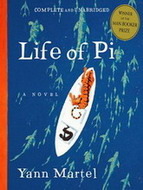
當然李安還是實驗了不少視覺把戲,片中二度改變銀幕比例(aspect ratio),飛魚成群飛撲小船的戲中,李安透過上下遮黑把1.85:1 的標準銀幕拉寬變成2.35:1的寬銀幕比例,當鏡頭隨著飛魚的觀點,穿梭於海面上下,躍起的3D魚尾巴更張揚地在畫框外擺動;第二次他則讓畫面比例接近垂直,用神般的鳥瞰角度拍攝Pi與老虎臥在船上,海面下可看到魚群游過,這個鏡頭設計其實是向原著封面致敬的巧思,也適切地烘托了海上空蕩、死寂的氛圍。
片中豐饒的意象、視覺符號,不只是流動的風景拼貼,更與角色的情感、故事的意涵,緊緊扣聯。本文試圖從視覺形式、符號涵義,說明本片如何透過電影語言,來體現原著的複雜文本,並注入李安獨到的新穎巧思。
鏡像與疊影的隱喻
從童年開始,Pi在理查身上看見自己的人性;但船難後的漂流旅程中,理查帕克則體現了Pi的獸性。兩者看似外在分離的個體,實則為內在拉扯的孿生鏡像。
童年Pi在動物園籠中,隔著鐵欄杆與老虎對望,那是Pi對現實世界的啟蒙,也是片中人性與獸性的交錯辯證的起源。父親教誨孩子:老虎沒有靈魂,所見的只是人心情感的映射。然而,人性/獸性的二元界線,就像當時將Pi與帕克隔開、看似牢不可破的欄杆,實則存在巨大的縫隙,存在著被穿越、顛覆的可能。
鏡像的符號很早就出現在電影中,媽媽紀所游過的清澈泳池倒映著湛藍的天空,彷彿自天際划水而過。這個超現實的意象,也出現在Pi遇難漂流後的海面,夕陽將雲朵染得橙黃,海天倒映、融為一景,救生筏上孤伶的Pi被巨大的鏡像所包覆,換言之,Pi的漂流並非是僅外在世界的歷險,更是內在的自我映照、省視與蛻變。

▲全片充滿鏡像的隱喻,奇幻的海面正如一面巨大的鏡子
片中的攝影鏡位安排,強化了鏡像與疊影的隱喻,一般的雙人反拍鏡頭(shot-reverse-shot)鮮少讓被攝者直視鏡頭,但本片卻大量以近乎等比例的正面特寫來對比Pi與理查的臉孔,除了突顯衝突張力外,此手法更有「對鏡自照」的象徵意味。尤其一場迷茫星夜的戲中,當時Pi喪失生存物資,意識漸趨混沌,他望著帕克背影,問牠看見什麼?接著Pi往海面一看,視線潛入深海的浩瀚奇景,看見母親的臉孔、蓮花的圖騰、以及幽冥海底的沈船;隨後鏡頭高速抽離、浮到現實水面,上頭卻是漂著帕克的倒影,換言之,Pi是透過理查的眼睛,去體悟到自然界生死循環的定律,並且直視自己的傷慟陰影,沒有這隻老虎的「托寓」般的存在,他永遠無法理清自己的悲慘命運。
在「神之風暴」的驚濤駭浪中,Pi與老虎躲在飄搖的浸水船艙中東倒西歪,此時導演更刻意混淆、錯置Pi與老虎的視點,迷亂中一度讓人分不清Pi與老虎的關係位置。除了鏡像的擬仿、身分的錯亂之外,當Pi與帕克出現於同一畫面時,構圖上前景、背景的人與獸姿態極為相仿,宛如疊影般的分身,預告中一場被剪去的戲,更讓Pi伏行在船上、以野性的眼神瞅著帕克,一再暗示了這是一場Pi「由人成獸」的變形記。

▲預告中出現正片被刪去的一幕:Pi如獸般伏行,與理查對望
理查帕克的三位一體:獸性、人性、神性
在表層的敘事意義上,帕克是一隻伴隨少年漂流海上的猛獸,代表自然界非理性的凶殘,而這隻從荒野撿回的老虎陰錯陽差地被取了個人名,絕非巧合。(註1)
西方神話中的英雄歷險多半有降伏野獸的情節,其不僅代表人類征服自然的優越,更蘊含著人類馴化內在的野蠻、蒙昧,超脫自然至文明與理性境界的意味;因此Pi在船上的「伏虎」過程,無論你相信哪個故事版本,都可以被視為與內心獸性的對抗。當男孩從安逸的生活,墮入了海上弱肉強食的險境,從小被灌輸的科學理性、宗教慈悲只能被擱置一旁。起初,Pi還試圖憑藉著理性求生,研擬生存與馴獸計畫,在船上劃分出人/獸的位階與領域,並透過書寫文字保持瀕臨崩解的理智,但隨著一次次的凶險襲來,原本弱肉強食的對峙兩方,卻越來越像相依相存的生命共同體。
套用粗淺的精神分析術語來看船上的空間配置,鎮日躲在小船底層的老虎,或許可被視為壓抑於潛意識、象徵本能原慾的「本我」(id),而不能殺生的宗教戒律,則是讓Pi克制自己莫淪為「野獸」的道德超我(super-ego),整段漂流中Pi不斷試圖將帕克壓制於下方、爭奪小船主宰權的對抗過程,便可引申為自我意識(ego)與潛藏獸性間的拉鋸戰。尤其理查在漂流之初幾乎從未現身,直到鬣狗殺害紅毛猩猩,Pi怒火中燒之際,牠才從Pi的「正下方」猛然躍出,「代替」Pi完成了他的復仇,兩者互為一體的對應關係,無需主人翁在片尾的懺情自白,早已不言而喻。
但在人/獸之外的另一種層次上,帕克的存在更宛若宗教神祇般的象徵,人對著虛空中看不見的神明祈福消災,深信著上天對人類的眷顧與慈愛,此般巨大的集體情感投射乃是單向而非雙向流通的,我們對神的信仰缺乏實體證明,完全屬於主觀感受,而正如同童年Pi相信老虎也有靈魂、飼主深信寵物也愛著自己一般,相信「老虎」的存在,就等於是相信了「神」,以真假難辨的動物故事來對照信仰的本質,便是這個半寓言的生存故事最聰明的地方。
(印度的宗教藝術中不乏老虎的圖騰,破壞神濕婆常以坐臥虎皮的形象現身,力大無窮的他曾有徒手屠虎的傳說,這除了象徵強大的力量之外,更代表神之所以超越凡人,乃是因為其能主宰內在的獸性欲念;另一幀18世紀印度蒙兀兒帝國「勇士伏虎」的繪畫中,獸中有人、人中有獸,互為彼此拉扯的一部份,而這個動物混雜拼貼的圖像,更成了電影中某個視覺意象的靈感泉源。)

▲18世紀印度蒙兀兒帝國「勇士伏虎」的民間繪畫
李安作者論:二元符號的曖昧對立與動態平衡
從作者論的角度看李安,在「父親三部曲」之後的作品多為文學著作改編,但這些作品橫跨了各個年代、時空、類型,似乎難以統整出一貫風格或主題。
李安曾在訪談中提到自己是「劇場」出身的人,吸引他的題材時常具備某種戲劇衝突的張力,從此脈絡觀之,從李安的作品總看似溫和大氣,沒有劍拔弩張、顯而易見的對抗力量,但的確可以捕捉到某種共通的二元對立特質,它可能是價值之間的衝突(理性與感性)、人與人之間的糾葛(李慕白與玉嬌龍),人與環境之間的矛盾(同志牛仔與懷俄明州),或是內心的天人交戰(綠巨人浩克)。
然而李安對戲劇衝突的詮釋不是爆裂的撞擊,而是二元符號彼此的曖昧催化與轉變。比方《臥虎藏龍》中的李慕白與玉嬌龍的互動關係,表面上是儒家長者與野蠻千金對寶劍的你爭我奪,但象徵禮教的李慕白卻在這場追逐中,逐漸被玉嬌龍誘發出某種近乎情慾的征服與占有欲望,換言之,李慕白這個清高「儒者」的符號所對抗的不只是一個蠻橫的年輕少女,更是自身內在如「臥虎」般被壓抑的欲念(無論是對玉嬌龍實質的肉體,或是她所象徵的青春與不羈);《理性與感性》的姊妹,姊姊看似拘謹自制,妹妹縱情追愛,壓抑與外放的兩人彼此對照又相互牽引,直到結尾姊姊與心上人重逢後淚如雨下,才訴說了這個角色情感澎湃的一面。
將人心內在的衝突與壓抑,以迂迴溫和、細密綿長的方式呈現並化解,或許可謂李安的某種「作者印記」。以此觀之,少年Pi之中對人性/獸性的詮釋並非是水火不容的異已、有優劣階序的價值選擇,而是彼此互通,甚至必須共生存在的動態平衡。
創造與毀滅、安逸與凶險互生的宇宙觀
二元符號的對立、單一線性史觀是西方創世神話的特質(神與魔、正與邪、創世與末日),然而《少年Pi》中流露出的宇宙觀卻明顯選擇了東方式(尤其是印度教)兼容並蓄的循環史觀。
無論是Pi所見幻象中的深海燈籠魚,或是風暴中自烏雲透出的神祕溫暖光芒(其實是致命的閃電),都看似某種虛假的救贖,暗示著自然界中沒有真正的寧靜安逸,毀滅與凶險往往伴隨著希望而來,但若缺少了它們的存在,意志軟弱、欠缺警惕的人們又無法在自然中生存。
這不僅是「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儒家訓誡,背後其實更蘊含了某種「生存/毀滅」實乃一體兩面的宗教寓意。
毗濕奴的漂流:死亡/新生、幻夢/現實之島
從「信仰」為出發的《少年Pi》融匯東、西方宗教意象,除了顯而易見的諾亞方舟(Noah's Ark)、屢受磨難且喪失至親的約伯(Job)、或是漂流海上被巨鯨吞噬的先知約拿(Jonah),都是西方家喻戶曉的舊約聖經人物。但最關鍵的神話典故,或許應屬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毗濕奴(Vishnu)。
毗濕奴(Vishnu)在印度神話中有著多重化身,曾化為魚與龜解救世人、參與創世神話(如同在大海中以肉身讓Pi得以活命的魚與海龜)。但片中最重要的典故應屬毗濕奴的宇宙之夢(cosmic dream)。傳說中毗濕奴躺在大蛇阿南塔(Ananta-Shesha)盤繞如床的身上沉睡,漂流於宇宙之海,而他所作的夢即化為現實中人間的宇宙循環──「劫」,毗濕奴睡夢時他的肚臍長出蓮花,從而誕生梵天(Brahma)創造世界,而每逢一劫之末,破壞神濕婆(Shiva)又毀滅世界。毗濕奴如此反覆沉睡、甦醒,宇宙隨之循環、生生不息,更有趣的是,毗濕奴的夢宛若海中的氣泡般繁多,每個夢都是一個獨立存在的小宇宙。

▲印度神話經典中,有著許多關於毗濕奴與其分身的漂流神話
這個曾被Pi短暫提及、有幾分神似莊周夢蝶的神話,無疑是全片最重要的宗教符號,它訴說了新生/毀滅、現實/幻夢的二元循環力量,而守護神毗濕奴扮演了這兩股力量的中介,維繫著宇宙的平衡。世界構築於幻夢之上,覆滅於清醒時刻,真實和虛幻有著同樣強大的能量,每個版本的故事都是並存不悖的宇宙。
當Pi漂流至長滿榕樹的浮島而重獲新生,看似安逸平靜的樂園中,那白日清澈的淡水在夜晚卻化作巨大的酸液池,而這座彷彿死亡陷阱的島嶼,在拉開的遠景充浮現出完整面貌──一尊躺臥的人形。這座漂島有許多可能的詮釋,它可被視為表面物質富足、實則精神死亡的偽救贖、假樂園;亦有論者視其為世俗化但喪失靈性的宗教組織(群聚的狐獴或許可引申為盲目膜拜的信眾)。
但有別於書中驚悚的描述,電影中的Pi在發現漂島真相後,並未視其為不祥的凶厄之地,反而認為神將他領至這個避難所,使其重獲新生,後來又在冥冥中給了指引,使他完成未竟的漂流。因此在李安的詮釋下,島嶼並非僅是駭人的死亡幻影,更是某種生存與毀滅交替、夢境與現實交纏的巨大隱喻。
如此觀之,漂流於宇宙虛空、在夢中創造現實的毗濕奴,便是人形島最可能的一種詮釋。(註2)
原著中的「藻島」在電影中被換作「榕島」是別有用心的安排。榕屬的菩提樹乃印度教中的聖樹,一般樹木朝天開枝散葉,但榕樹空中懸浮的氣根,到達地面後卻插入土壤、持續向下蔓生,漸與樹幹交融一體,此種雙向生長的特性,使得印度教經典將榕樹與其水中的倒影,作為現實與靈性世界的對應象徵。在古老的史詩中,更有許多毗濕奴與榕樹的相關傳奇。例如先前提到漂流神話的另一個版本中,毗濕奴的至聖人格化身──黑天(Krishna)在末世洪水中以嬰孩之身漂浮於榕樹葉上,口中含著宇宙,免於它遭受毀滅。

▲上下顛倒的榕樹在印度教中被視為與現實對應的靈性世界
還記得開場的動物園群像中,那隻與榕樹樹根交纏的蛇嗎?牠除了是西方「失樂園」神話中的重要角色(李安曾說男孩被迫舉家搬離從小長大的動物園,就是他所喪失的純真樂園),更與毗濕奴躺臥於大蛇身上漂流的傳說有了幽微而遙遠的呼應。
不可思議的奇幻漂島,循環著生與死的力量(如同創造神梵天與破壞神濕婆),形成一種奇妙的生態系統(如同維持著世界平衡的守護神毗濕奴),它更是一個巨大的心靈圖騰,承載了夢作為現實擬像、甚至根本就是現實的可能性。
蓮花的隱喻:包藏死亡秘密的真相、超脫罣礙的神性花卉
毗濕奴的漂流神話與榕樹的隱喻耐人尋味,除此之外,片中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神祕符號──蓮花。以人物觀點來看,蓮花無疑是Pi與母親及女友阿南蒂的私密情感連結,無論是童年時母親在地上畫著蓮花的情景(在海底幻境中被放大成巨型的圖騰),或是日後詢問阿南蒂「蓮花」舞蹈手勢意涵的戲,再再說明了Pi對兩人的思念。但若將這個象徵延伸到更寬廣的文化脈絡,意義層次愈顯豐富。
希臘荷馬史詩《奧德賽》中,主角與其士兵攻破特洛伊城後,在返鄉途中漂流到一個長滿蓮花的神祕荒島,上頭的居民款待蓮花與果實給他們享用,這些蓮花卻有著迷幻藥的麻痺作用,使這群疲憊的士兵昏沉欲睡,忘卻了自己的故鄉,不再想返家。

▲荷馬史詩中,奧德修斯的水手吃了荒島上的蓮花果實後昏沉欲睡、忘卻家鄉
這個宛若孟婆湯的植物,在印度教中則有看似相近、又截然不同的意涵,它一方面是創造力量的神性花卉(毗濕奴肚臍長出蓮花,梵天誕生其中),在修行上則代表了超脫俗世、心無罣礙的清明境界(因其漂浮於水上,不沾染水底汙泥),是心靈的極致演化,意識的中心點。學會放手、不再牽掛,是主角面臨的重要成長課題,因此海底幻像中的母親與蓮花,既是親密無比的回憶,又隱涵了離別的傷感喻意。
希臘史詩中的蓮花果實讓人遺忘歸鄉,但Pi 當剝開貌似瓣瓣蓮花的果實後,卻反而窺見了島嶼食人的真相,進而清醒並踏上返鄉旅程,蓮花看似包藏「死亡」的符號,但Pi認為那是神賜予他「生」的訊息,使其看透事物表相,逃過一劫,並且領悟自然中的生死與無常。
如同Pi本人身兼動物學與宗教學家身分,故事中繁瑣的動、植物符號,架構了起第二層的情節想像,更牽引出一連串潛在的宗教與文化蘊義。當然觀影並非詮釋與解謎的競賽,老虎可以只是老虎,蓮花或許也不具深意,符號迂迴多義、若有似無,創作者丟出線索卻不提供明朗解答,如同電影的開放結局,任憑信者上鉤,這些符號的曖昧本質,又導向了影片的另一個主題:故事。
故事就是我的信仰:虛構的魔力
好萊塢拍片時常喜歡拍兩個結局,經小型團體試映(test group)過後,才決定採用哪個版本,但李安在《少年Pi》中卻直接在結尾提供了「兩個故事版本」的選擇,當片中記者/片外觀眾追問哪個故事才是真的?眾多動、植物符號如何對應故事角色與情節?又具備了何種意義?導演卻像一去不回頭的理查帕克般,逃逸至符號繁密的森林中,不提供任何確切答案,留下極為開放的詮釋空間。
電影的時序不斷在成年Pi的回憶、少年Pi的現實之間迴旋,對於部分觀眾而言,它破壞了故事的流暢感,讓沉贅的口白取代了視覺體驗。旁白(voice-over)的運用在許多人眼中代表了創作技法的拙劣,使人情感抽離、無法融入。但對於這部電影而言,「敘事框架」(diegesis)卻是這個「關於故事的故事」的必要元素,若少了成年Pi作為旁白者的中介口述,結尾便會失去曖昧的多重想像。
許多人說這部電影讓人相信神的存在,但李安對於「神」的探索始終源自於人心,「敘事」的魔力或許才是他真正關切的焦點。古人面對混沌的自然、複雜的人生,用神話敘事來解釋天地起源、萬物興衰、生死宿命,這些故事讓人從混亂中得以理出因果邏輯,進而接受、釋懷,神話所構築出的信仰,更是支撐人生存下去的心靈力量,如同整部片劇情主幹的第一個故事版本,它神奇、動人、卻超出理性可理解的範圍。
英文俗諺「看見即是相信」,電影《贖罪》(Atonement,2007)結局中,女作家坦承自己虛構了另一個人生故事,作為生命走到盡頭前的最後一絲溫暖善意與救贖,並拍出了殘忍的真相,相較下,少年Pi吐露的第二個版本卻僅以長鏡頭獨白呈現,未有具體影像的演繹,對照於先前一百多分鐘的視覺奇觀,完全是虛空的言語,換言之,這個版本並未「取代」前者、「揭露」真相,顯得無比曖昧。聆聽者選擇的答案代表了不同的信念與價值,從原著到電影,皆保留了兼容並蓄的人生態度,夢境與現實間沒有「真」或「假」的主客區隔,虛構的夢有時才是唯一的真實。
電影中繁多的象徵符號、寓意,有著無窮詮釋與翻轉的可能,導演在電影座談會中,對劇情意義的解釋語多保留,不願給出正解,因為他也明白符號學的「衍異」(differance)難題,一個符徵不可能完整涵納、對應另一個指涉物,符號系統串聯的是無止盡的縹緲意義鎖鏈,正如宇宙中的圓周率定理僅能用π的符號化約,並無法用已知的語彙去完整界定、表述,那無盡延伸的數字,就像我們試著用有限文字、影像去捕捉「真實」一般,僅是徒勞無功的嚐試,因為生命中並不存在唯一、絕對的故事版本。
儘管如此,人們仍不休止地說著一個又一個,關於自己、關於他人、關於世界的故事,因為在這混沌人世中,敘事理清了我們的思緒、構築了我們的信念、解答了我們的迷惑,人生是無盡且無常的流離漂泊,故事所帶來的能量,是我們唯一可依憑的一葉扁舟。
【註1】愛倫坡(Edgar Allen Poe)的長篇小說《海上歷險記》(The Narrative of Arthur Gordon Pym of Nantucket,1838)中有個遭逢海難後被同伴抽中吃掉的水手,就叫理查帕克;1884年某艘遇難的英國遊艇上,一名被同伴殺害、吃掉的17歲年輕水手也剛好名為理查帕克,原著楊.馬泰爾在蒐集海難資料時發現了這些驚人的巧合,便刻意引用這個姓名。
【註2】曾參與電影前製籌備、調查研究工作的Jean-Christophe Castelli在其撰寫的幕後製作專書中,即已說明片中的神秘孤島影射了毗濕奴的漂流之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