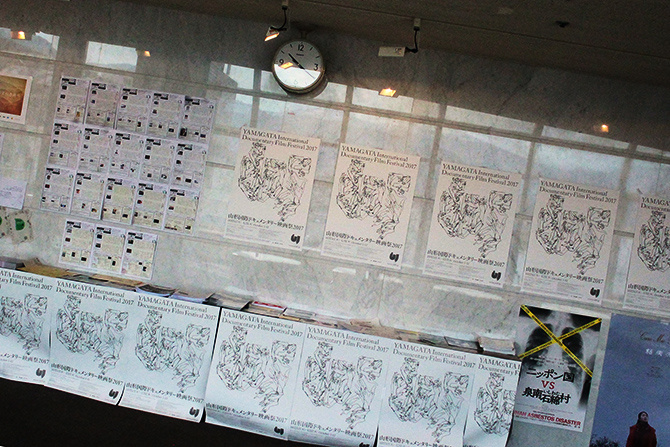拍攝者與被拍攝者共同創造的世界
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YIDFF,以下簡稱山形影展)自1989年創立以來,兩年舉辦一次,今年(2017)已邁向第十五屆。今年影展於 10 月 5 日 至 12 日展開,活動開始前一個月,舉凡鞋店、雜貨店、居酒屋,影展海報已遍布在城市各處。耳聞山形影展一直有很強的在地連結,與志工們聊天下來,參與者常常動輒十年起跳,兩年一次的準備與等待,除了包括當地居民的支援,也有人從山形市周圍城鎮慕名而來。
本屆影展共有來自 128 國家與地區,投件作品達 1,791 部,選片部分不吝於打破固有紀錄片真實與虛構疆界,更不乏前衛與實驗性高的作品。開幕片為紀念今年剛逝世、以實驗電影著稱的松本俊夫(Matsumoto Toshio),以16mm、35mm放映三部短片作品,其中,《右眼開始受擠壓》(つぶれかかった右眼のために)更原汁還原,用三台16mm放映機同時放映,銀幕上疊影閃爍,直接將日本60年代的社會躁動傳遞出來,令人大喊過癮外,也對放映團隊硬底子的功力深感佩服。今年是我第一次參加山形影展,對親切的在地志工與自由獨立的影展氛圍留下深刻的印象,以下是幾點在影展的觀察和報導。
國際競賽與亞洲新力──
高舉國家壓迫下的勇敢公民
山形影展的國際競賽單元有別於一般選片認知,強調由「真」人(“real” people)觀點出發,強調人本精神,選片團隊除了影展工作人員和電影學者,更包含當地小企業家與影展志工。繼上一屆有334分鐘的《家園—伊拉克零年》(Homeland (Iraq Year Zero),2015),今年國際競賽一部比一部長,包含中國導演朱聲仄的《又一年》、費德瑞克‧魏斯曼(Frederick Wiseman)的《歡迎參觀紐約市立圖書館》(EX LIBRIS -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片長超過3小時的影片就有4部,場次之間往往只有90分鐘不到的休息時間,短時間內要消化大量資訊,迎接下一部影片,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理事藤岡朝子(Fujioka Asako)也表示今年對評審來說是特別辛苦的一年。
本屆國際競賽單元的首獎「弗拉哈迪獎」(The Robert and Frances Flaherty Prize)由在台北電影節放映過的波蘭作品《信望愛之家》(Communion,2016)拿下,而敘利亞導演Alfoz Tanjour《卡其色的記憶》(A Memory in Khaki,2016)藉由卡其色的象徵──既是軍人也是學生制服的顏色──記錄五個人對敘利亞獨特的複雜情感,拿下「山形市長賞」。「優秀賞」則由拉烏爾佩克《我不是你的黑鬼》(I Am Not Your Negro,2017)與中國導演沙青《獨自存在》獲得,巴西導演João Moreira Salles的《激情時刻》(In the Intense Now)則像篇影像論文(essay film),將三段1969年的重大事件交叉剪輯,密集的旁白與影像素材反覆辯證,獲得特別賞的肯定。
已經72歲的原一男仍犀利未減,新作《日本國VS泉南石綿村》(Sennan Asbestos Disaster)記錄大阪的泉南地區歷時八年的石綿賠償訴訟,雖然長達215分鐘,影片本身卻張力十足,細膩明快地剪輯大刀闊斧地對影片進行裁切,彷彿節奏感也是武器之一。上半場訪問受害者家屬,穩紮穩打,下半場風格一轉,直接介入影片提問(看過原一男之前作品的觀眾應該會湧現熟悉感),政府一面罔顧人命、持續與患者及其家屬官司上訴,一面維持迂迴的繁文縟節,除了幾近片尾時的回馬槍:漂亮地讓日本官僚體制打了自己一巴掌,原一男更關注運動本身參與者的異質性,突顯出從片名《日本國VS泉南石綿村》中原一男所選擇站的位置。兩場映後Q&A抗爭者也來到現場,全場觀眾看得又哭又笑,順利奪下觀眾票選獎的市民賞。
本屆「亞洲新力」(New Asian Current)單元投件作品共為645 部,來自63 國家與地區,首獎「小川紳介獎」由香港導演陳梓桓《亂世備忘》(Yellowing,2016)拿下,別具意義。領獎時陳梓桓感謝所有被攝者,希望各方持續關注香港的政治情勢。優秀賞則由韓國導演Song Yun-hyeok《The Slice Room》與印度Anushka Meenakshi和Iswar Srikumar執導的《Up Down & Sideways》獲得,緬甸華僑趙德胤的《翡翠之城》和韓國鄭潤錫的《龐克海盜地獄首爾》拿下特別提及獎。
其他值得一提的競賽片,像《唐吉訶驢》(Donkeyote)會在今年金馬影展放映,故事雖小卻簡潔真摯,傾斜緊貼驢子的鏡頭魅力十足,展現導演渾然天成的視覺感。荷蘭導演伊斯特(Ester Gould)的《A Strange Love Affair with Ego》,透過四位女性折射人們在當代社會中對受到關注的渴求,但觀點的選擇與字卡運用,顯得影片在敘事策略上還有尚未解決的矛盾。《卡拉布里亞》(Calabria)則拍攝兩名瑞士殯儀館工作人員將一具屍體送回義大利卡拉布里亞,影片大半部都在車子內進行,五組鏡頭輪流剪接切換,樸素的外表下場場有戲,兩位迷死人的素人漫談,信手拈來道出瑞士二代移民的文化。
原一男導演(右二)與紀錄片被攝者(左一至三)出席映後。(攝影/鄭雯芳)
逝者猶未安魂,傷痕依舊需要撫平──
311後山形影展的持續記錄與行動
《Tremorings of Hope》劇照。《Tremorings of Hope》劇照。立「Cinema with Us」單元,持續關注海嘯與福島核災對居民與日本社會的影響,希望引發觀眾思考紀錄片在行動中所扮演的角色,雖然至今年已是第四屆,在某些地區仍有人因海嘯下落不明,災難的創傷並沒有隨著時間輕易消褪。
伊藤憲的《怪物君:吉增剛造和震災》紀錄日本當代著名詩人吉增剛造,在311後嘗試以影像及聲音創作詩作《怪物君》的過程,算是展覽的錄像作品。較具代表性則是大地震前,已在波伝谷村進行民俗學調查的年輕導演我妻和樹,畢業後拍成《在波伝谷生活的人們》(The People Living in Hadenya),記錄了尚未遭受海嘯的小村風情。新片《Tremorings of Hope》則入圍今年國際競賽單元,延續前作紀錄地震後波伝谷的人們被分散到不同的組合屋區,希望透過傳統獅子舞的祭典召喚昔日的團結力量,觀察村民對復甦的渴望和懷疑。
《在波伝谷生活的人們》以蹲點、考究的方式,捕捉了村莊各行各業旺盛的生命力與傳統人情,其實也是支持導演持續紀錄的動力之一,續作《Tremorings of Hope》投入了大量的情感,無法割捨的篇幅在整體上難免讓人覺得失衡,但當「重建」(Recovery)在日本社會每年被儀式性地提起、逐漸成為意義不明的政客語言,兩部影片橫跨了災難前後,彼此對照,展現紀錄片介入現實,改變攝者與被攝者的生命,呼應了「Cinema with Us」單元的終極意義。
《Tremorings of Hope》劇照。
2017山形影展專題聚焦──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佛瑞迪穆勒、松本俊夫與佐藤真
繼前幾屆阿拉伯專題的關注觸及到北非,本屆將主題延伸至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觀點」(Africa Views)介紹22部2000年後的作品,描繪當代非洲的樣貌。一向重視紀錄片與政治關係的山形影展,今年也回顧了70年代至80年代巴基斯坦與黎巴嫩。導演專題方面則包括瑞士導演佛瑞迪穆勒(Fredi M.Murer)與日本導演松本俊夫,讓人飲恨的是,影展在4、5個場地同時放映,除了競賽與「透視日本」單元(Perspectives Japan),多數專題僅放映一場,今年因觀看國際競賽長片耗去不少時間,奔波之間犧牲了上述兩位導演和兩項政治專題,僅看了另一位佐藤真導演的回顧。
今年「山形與電影」單元以紀念佐藤真這位推動紀錄片的先軀作為企劃核心,帶來「山形銀幕復興!」(Yamagata Silver Screen Revival!)、「十年旅行:佐藤真,紀錄片的現在與未來」(Ten Trips Around the Sun: Sato Makoto’s Documentary Horizon Today)、座談與講座、紀錄劇場《Everett Ghost Lines Version B-Faces》,具有奠基過去、檢視現在、展望未來的意味。
我看的兩部短片:《SELF AND OTHERS》和《阿賀的記憶》(Memories of Agano),素材都是16mm拷貝。《SELF AND OTHERS》是佐藤真將36歲便英年早逝的攝影師牛腸茂雄生前留下來的攝影照片、書信以及錄音製作成53分鐘的短片,靜態的照片、生前的遺物、生活的街道、過去錄下來的聲音,散發出強烈的生命力。另一部《阿賀的記憶》從一個樹林間張起大大的白幕,放映十年前製作的《生活在阿賀》開始,慢慢帶觀眾回到十年後的阿賀,本片乃延續自1992年記錄新瀉縣阿賀地區的水俁病受害者的《生活在阿賀》(Living on the River Agano,1992)。佐藤真回到阿賀看看當年那些居民,以及依然荒蕪的稻田、無人居住的房舍。攝影機帶觀眾凝視著居室裡正在爐上燒煮的茶壺,時間像是靜止不動,而白煙緩慢上揚,畫外音是老婆婆笑嚷著不要拍她。阿賀地區的居民承受水俁病之苦,十年後是否被人們遺忘了呢?時間與空間在緩慢節奏的影格中,交錯出淡淡的宿命感。
特別企畫──「Roxlee’s Yakata」
這次另一個驚奇的收穫,即是藉著「亞洲新力特別企畫」認識了菲律賓藝術家Roque Federizon Lee(大家習慣叫他Roxlee)。喜愛畫畫的Roxlee大學時曾念過建築系,不過他很快就退學了,原因是厭倦了老是畫直線!退學後的Roxlee做過撰稿者、畫連環漫畫,僅用紙、筆以及天馬行空的幻想,便可幻化出各式多彩的作品,雖然從未在動畫產業裡工作,獨立製作及充滿活力的風格影響了年輕一代的動畫師,可以說是菲律賓獨立動畫電影的先驅。
自1989年參加山形影展起,Roxlee便與山形結下很深的淵源,幫忙影展日報畫卡通插畫、設計紀念T恤和周邊小物。本次影展除了選在離主場地不遠的舊西村寫真館作企劃覽展,還規畫了放映與表演。放映開演前,身穿咖啡色僧袍的Roxlee突然出現在會館廣場,用繩子拉著手托著槍的士兵模型在地方移動,嘴裡喃喃發出唸咒般的聲音,並拿出膠卷鞭打士兵,握著士兵的手在紙板上寫著「要電影,不要戰爭」,圍繞的觀眾被引起好奇心外,更被他天生的喜感引得哄堂大笑。
表演結束後,Roxlee拿出剪刀將膠卷剪成段,當作入場券讓觀眾象徵性的索票進場,放映作品為Roxlee的影像總集,包括動畫、劇情片、紀錄片。有些作品沒有對白也沒有字幕,主辦單位安排了辯士站在銀幕右方現場加入旁白,我尤其喜愛《Harajuku》與《The Great Smoke》,前者拍攝原宿街舞影,有著MTV的質感與強烈節奏,後者反覆利用素描的局部展現推動敘事,充滿不設限的想像力與童趣。中場休息時,Roxlee告訴觀眾如果想睡就安心睡,想回家就回家吧,他希望觀眾觀看電影是可以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
|
|
|
|
上左:Roxlee 表演;上右:表演後,Roxlee剪下膠卷當入場卷;
下圖:Roxlee作品《Great Smoke》。 |
|
「電影」就在山形
除了電影本身,影展期間還有許多周邊活動:配合非洲觀點主題的「非洲之夜」DJ秀、回顧佐藤真的紀錄劇場《臉》等,最為人稱道是在影展期間每日晚上10點至凌晨2點,只需500日圓即可入場超過百年的老店香味庵,導演、觀眾、影迷、志工,各種身分只要是愛好紀錄片的人,都能在這裡暢談電影、享用山形的鄉土料理芋煮。影展這項傳統也許是順應了紀錄片工作者的性質,機動性強、注重獨立,無須擺架子與撐場面,大家在香味庵平起平坐互相認識串聯,常常到凌晨2點店家鳴笛後,人潮還遲遲不肯散去。
山形重視人與人的交流在志工身上也顯露無遺。演出前一天傍晚,才從手冊裡瀏覽到致敬佐藤真的劇場演出,心急之下詢問了志工是否還能買票,沒想到志工立即放下手邊工作,細心地帶我穿越街道回到正在熄燈收工的辦公室,從收好的雜物中取票給我,讓人覺得有些不好意思時也備感窩心。而居民們對影展也有相當的認同感,在參觀舊西村寫真館時,九十多歲的志工小林和彥先生,緩慢地用英文和我們聊著這間寫真館的過去,經歷過二戰、美軍駐日,如今重新開放,不禁產生產生時間和空間錯置與事件交揉的魔幻感。說到底,山形的貼心款待真有種獨特魅力,宜人的氣候和生活步調讓人容易融入小城,經過街口轉角,咖啡店外即坐著昨天映後座談的導演,上前閒聊或打打招呼都是一種再自然不過的交流,影展塑造出的氛圍似乎是在鼓勵或邀請你,只要主動向前多跨一步,就會得到更豐富、屬於自己的山形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