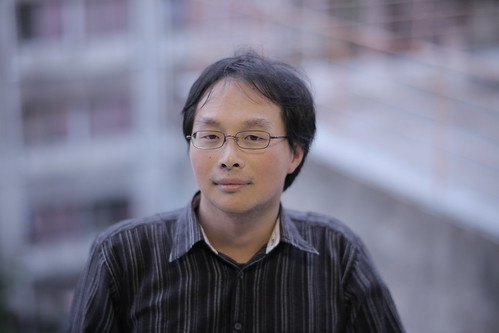異色年代:顫顫巍巍的甜蜜家庭──訪《臨淵而慄》導演深田晃司

不合理,是日本導演深田晃司(Koji FUKADA)對「家族」的形容。當我們打從一出生即處於懸崖絕境,生命中需面對多少與徬徨無所從?深田日前在台上映的新作《臨淵而慄》(淵に立つ,Harmonium)就是一部朝著家庭關係中幸福之光照不到的陰暗面深掘的作品。
謎樣的「外來者」八坂(淺野忠信 飾),他以一身白襯衫、黑長褲,彷彿神職人員般拘謹、肅穆的姿態,出現在利雄(古館寬治)家的工廠門口,一個令人不安的因子,即刻介入一家三口的現家庭。利雄與八坂是舊識,他們之間似乎有著不可告人的秘密。因此,利雄在告知妻子章江(筒井真理子飾)之前便雇用了八坂,並讓他立刻搬進家裡與妻女同住。電影的前半部,故事描述這個陌生人漸漸融小家庭,八坂溫和地教女孩小螢彈風琴、與章江聊起宗教信仰,陪母女倆一同上教會主日⋯⋯這些都是利雄不曾為家人做過的事。
「耶穌經過的時候,看見一個生來就瞎眼的人,門徒們向耶穌問道:『拉比,此人⋯⋯』」電影中,牧師在做主日傳道時,短短引用了該段經文,應是聖經中〈約翰福音〉第九章。電影裡未唸完的下文是:「『拉比,這人生來是瞎眼的,是誰犯了罪?是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穌回答說:『也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這也成了劇情的伏筆。電影的後半部情節,有突如其來的災厄、令人不解的惡意攻擊、被撕碎的家庭關係。
《放映週報》特別透過安排筆訪了深田晃司,請導演分享這部拿到坎城「一種注目」單元最佳導演獎的作品背後的創作概念。
深田導演在受訪中提到了他對生存的畏懼:死亡、生命的無謂以及孤獨⋯⋯這些細膩的感受,皆可經由片中之細節透露出來。藉著「外來的魔鬼」所觸動的毀滅事件,帶動整部電影的詩意、哲思與殘酷。而撇開作品的沉重發展,導演依然認為,人與人之間的破裂關係還是有修復的可能性。雖然人類無法完全互相理解,但能有盡力了解彼此的那份心意。家族即便充滿了太多不合理,卻不全然是絕望的。這些予盾,待觀眾細細地品嚐過電影,或許能在生吞驚恐並咀嚼苦澀之後,體會到生而為人的箇中滋味。
就導演的觀點,男性與女性在現代家庭中各自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深田晃司(以下簡稱深田):我認為至少在現今的日本,離男女平權的狀況還非常遠。舉例來說,日本現在仍然無法實施「夫婦別姓」(編按:婚後妻子不需冠上夫姓)的制度,政府至今依然支持傳統的家庭制度。現在如果要拍家庭題材的電影,創作者對這些現狀的觀點容易受到矚目。
《臨淵而慄》的時空背景是否有明確的參照,例如特定的時間點或地域?
深田:沒有具體的參考對象。不過在我渡過青春期的九〇年代,日本經歷了新興宗教的毒氣無差別攻擊和大地震等洗禮,這些對於現在青少年而言,可能難以理解的殺人事件、撼動社會的重大災難頻傳,那個時代讓人感受到我們的日常生活隨時有可能被不合理的暴力而瓦解。這段記憶應該有反應在八坂的暴戾個性上。
在您心中,「家族」中是否存在恆久不變的價值與羈絆?
深田:「永遠不變的價值與情感」這種概念,等同於信仰中的「神明」,相信的就是相信,但頂多就到這種程度。再者,在電影中過度鼓吹「家庭」的價值,等於排擠掉沒有家庭的人,所以我不會想特別提倡。
延續您以往的作品,《臨淵而慄》的世界觀是否更為悲觀?
深田:我不覺得這次的電影會特別負面。比如丈夫利雄的最後一場戲,看起來是心懷絕望還是希望,我覺得會因人而異。
導演作品中的恐慌感,是源自於什麼樣的焦慮?
深田:我覺得是罪惡感。其實我自己是不相信因果報應的人。但是人類就是在發生事情的時候,容易去思考因果關係的生物。我想描寫人類這種弱點。
在電影中佔了極大一塊的宗教信仰,對於角色來說是什麼樣的存在?
深田:很難用一句話來說明。宗教有時候是拯救人類的憑藉,但那對我而言已是過去的烏托邦。這部電影中的宗教,特別被描寫成一種「忘卻孤獨」的東西。然而,人一生下來就是孤獨的個體,但人無法一個人活下去,需依附在家庭或宗教等個體之下,才能忘卻孤獨活下去。而那些共同體的約束力衰退,即是一種現代化的象徵。為了描寫出普世人類擁有的孤獨,我先讓妻子章江先擁有信仰,之後再花兩小時慢慢剝掉。
片中人物的衣著顏色似乎暗示其處境或性格,這些顏色是否別具意義?
深田:顏色本身沒有特別的意涵。這部電影裡八坂這個角色一度消失在片中,我想表現出他即使不在,仍隨時支配整個銀幕的氣氛,因此在他最暴力的場面加強紅色的印象。後半不時在畫面中運用紅色,釋放出他的氣息。
最希望透過本片,傳達給觀眾什麼訊息?
深田:我拍電影的時候不會考慮要傳達的訊息。因為我不想把電影當作宣揚個人思想的道具。雖然沒有訊息,但我還是會盡量選擇普世一點主題。這部片並沒有在片中完結,希望觀眾能在看完電影之後,思考關於家庭、生命和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