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極限拍片,尋覓臺灣恐怖片新可能──專訪《詭鄉》導演馬新語

編按:2025 年,臺灣恐怖電影《詭鄉》由南加州大學電影學院碩士畢業、在美國擔任剪輯師的新銳導演馬新語執導;初孟軒、雷嘉汭、王滿嬌、張翰等主演,以鬼屋為題材,並嘗試納入心理驚悚元素,在恐怖片常態出現的市場中力圖新局。本期《放映週報》專訪導演馬新語,由片型與製作過程著手,分享盡可能透過恐怖片挑戰電影創作的過程。請見本篇專訪。
※※
舉著今年唯一「鬼月上映臺灣鬼片」大旗的《詭鄉》,融合時下年輕族群更能共感的「心理創傷」元素,大玩催眠題材。故事描述主人翁李昂,自幼於美國長大,帶著「傷」重返家鄉臺中梧棲,走進神祕詭譎的家族老宅。
夾著或多或少的自我投射 ,《詭鄉》出自旅美歸來的年輕導演馬新語之手。翻看他的作品集,從紀錄片到劇情片,橫跨喜劇、恐怖、奇幻、科幻等多元類型,多年來以剪接為主業的他,累積了紮實經驗。在當前臺灣恐怖片百花齊放的氛圍下,帶著在美國獨立製作的養分,聯手家族成員看準市場,打造屬於自己的恐怖 IP。
在電影首映結束的午後,自稱是「內耗 I人」的馬新語,依然全力開啟社交模式。從創作起點、開發田調到拍攝趣聞,能量滿滿地與我們分享製作《詭鄉》的心路歷程
──您在美國唸書後,很長一段時間待在那從事剪接工作。請先和我們分享,是什麼樣的契機讓您有機會返臺拍攝第一部長片作品?
馬新語(以下簡稱馬):我從美國南加大畢業後,進入了一間獨立製片公司,主要擔任剪接師,同時也會參與一些項目的開發。2023 年,我幫他們做了一部片的策劃以及剪接,我們用很低的預算拍了一部長片,結果真的有開花結果。我們拿到了一些獎項,也入選不少歐洲影展,頗有斬獲。而我的表姊,也就是《詭鄉》的監製陳頡昕,當時也有參與那部作品的投資,在那次經驗中,她開始對電影產生興趣,覺得我們是不是也可以來做一部自己的電影?
有了這個想法後,我們便開始構思,要拍一個什麼樣的電影。我自己比較想回臺灣拍,一方面是觀察到,我們這些到美國進修電影編導的留學生,不管是拍白人或美國文化題材,其實都沒有辦法拍得很深刻。如果是移民題材,好像又有點被拍膩了。所以我才想,那是不是可以回臺灣拍?就拍一個從美國回臺灣的人的故事吧。片中男主角李昂回臺灣的設定,就是這樣來的。
──剪接經驗曾讓您接觸到很多不同類型電影,自己的第一部劇情長片又為何選擇恐怖片?
馬:題材的選擇,主要有兩個考量。其一是我的家族有非常多有靈異體質的人,這是一個我們蠻有感覺的題材 ;再者是以臺灣電影市場來講,鬼片還是相對容易去推行的一個類型。基於這兩個前提,我和監製便開始構思故事。
從一開始的構思階段,我們就以「最能節省成本」為前提來發想。很快地,監製就提議可以用她家來拍攝。那棟位於臺中梧棲的房子,傳說是所謂的「陰陽交界口」。我們都覺得「去鬼屋拍片」這件事本身就很有趣,再加上臺中也是我們的家鄉,如果選在這裡拍攝,相對也會有更多的人脈可以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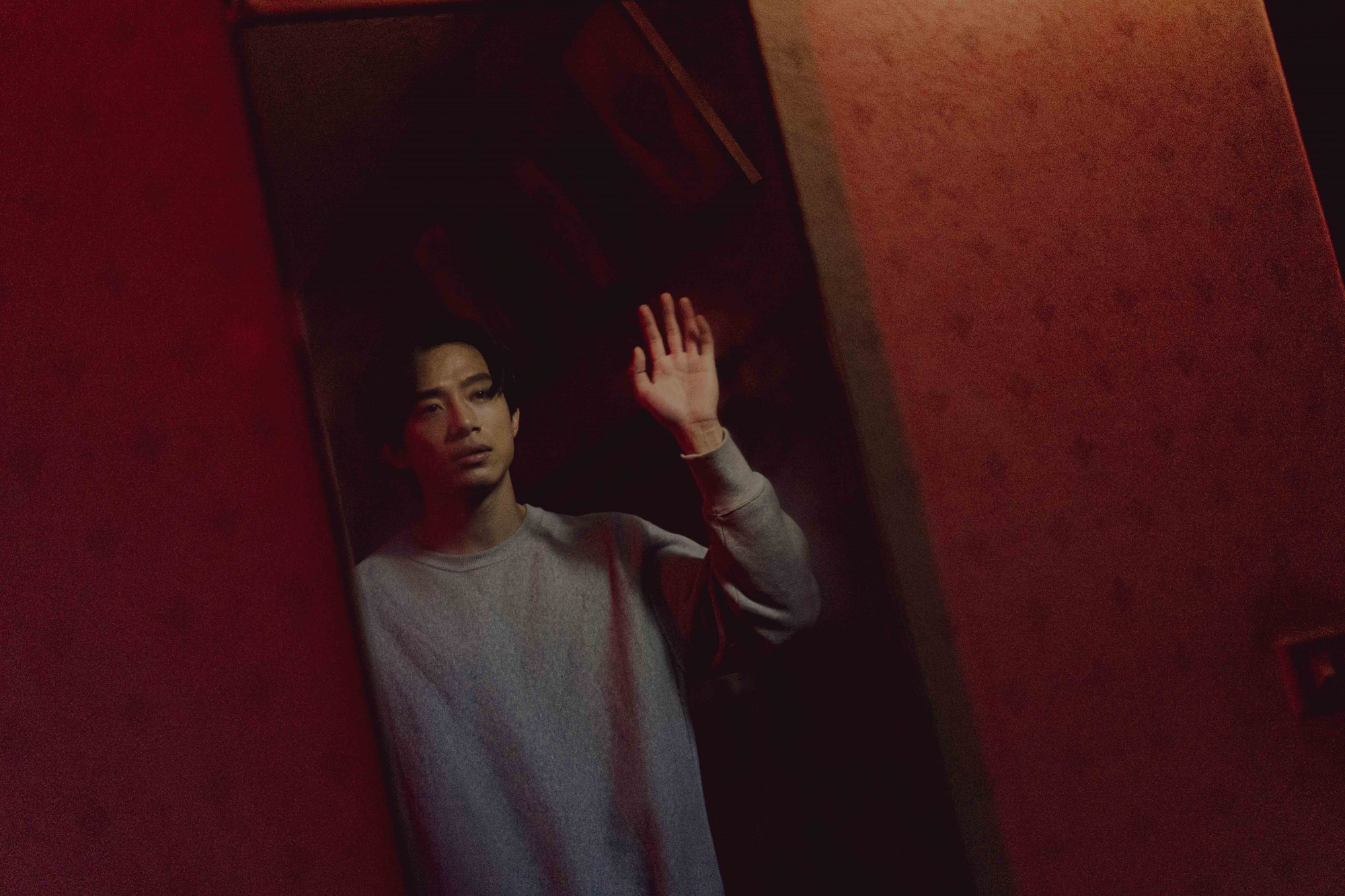
──也就是說,團隊是先鎖定了場景才開始發展故事?您提到故事的開發是基於成本考量出發,是否在創作劇本時也都將所有預算的限制想進去了?
馬:沒有錯。當時監製就先問我,如果要在最有限的預算下把片子拍出來,有什麼注意事項。我告訴她,第一是「角色不能太多」,再來就是「場景最好限制在幾個地方」。所以是用這幾個角度去發展故事,而我在寫劇本時,也確實把預算放進考量裡。
比方說,我們很明確地把主場景設定在家族的老宅,其他場地也優先參考臺中協拍的資料庫。這些資源都直接幫我們省下不少場景支出。同時,把場景侷限在彼此不遠的幾個點,劇組就不需要每天移動來、移動去,現場拍攝效率因此提升。另一方面,我自己本身是剪接師出身,這些經驗有助我在分鏡上的思考,減少了很多不同角度的拍攝,讓現場效率更高。
其實,我們總共只花了15天就把這部片拍完(笑)。當然,這也是一開始就設定好的拍攝天數。整體來說,可以說是用有點「極限操作」的方法,達到節省成本的目的。
──您提到剪接背景幫助你思考分鏡,進而提升了拍攝效率。請和我們多談談,您過去的經歷,那對您投入導演工作還帶來了什麼幫助或優勢?
馬:我在臺藝大電影系念大學時,就對剪接比較有興趣。不過當時還是流行導演自己剪片。現在聽說系上已有專門的剪接課,越來越多學弟妹選擇專職做剪接師,真的進步很多。
那時候我覺得只當導演難以養活自己,需要一個副業,而剪接師或許是選項。到美國南加大後,我主修導演與剪接,因而在校內累積了一些名聲,畢業後也透過學長姐介紹工作機會。
真正的成長是從短片跨到長片的剪接。這兩者的思維完全不同,我先後接觸過兩次長片,也從合作導演身上學到許多技巧,算是為自己拍片做好準備。不過在《詭鄉》裡,我仍找了一位剪接搭檔,畢竟身為導演,容易割捨不掉某些場景,需要另一雙眼睛幫我把關。
──您有什麼特別喜歡的恐怖作品或深受影響的導演嗎?
馬:我很喜歡國片《屍憶》(2015),它的劇情紮實,也很恐怖,成功之處在於大量運用特殊化妝營造氛圍。這一點我也放進《詭鄉》裡,比起電腦特效,片中鬼的呈現主要都是靠化妝完成。另外,去年韓國的《破墓》(Exhuma,2024)我也很喜歡,尤其是前半段壓抑、詭譎的氛圍。我們在後期製作時看到了這部片,它的剪接節奏確實給了我們不少啟發。
至於影響我的大師,答案可能和很多人一樣(笑),就是克里斯多福諾蘭(Christopher Nolan)。我很喜歡他處理記憶層層疊疊、反轉不斷的設計,在《詭鄉》裡我也嘗試做了類似的設定。
──主角是一個在海外長大,返回父親家鄉的年輕人,這個角色的設定帶有您自己的投射嗎?請和我們談談您設定這個角色的起心動念。
馬:我每次回臺灣,都會有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和片中主角的設定不同,我是在臺灣念到研究所才去美國,但回來時仍常想,不知道哪邊才是「家」。在臺灣又待久了會慢慢熟悉,但每次剛回來又總有種奇怪的陌生感。我很想把這種感覺放到初孟軒飾演的李昂身上。對他來說會更強烈,因為片中是設定他第一次來到臺灣。
角色面對壓力、焦慮的部分,其實也有我的影子。我是一個比較內耗的人,常常給自己很大壓力,表面看起來陽光,但內心還是有點陰暗。在角色上,我把這層陰暗放得更大。而演員初孟軒剛好也有這個特質:外表陽光,眼神卻帶著憂鬱。他不是 ABC,但身上有那股氣質,英文也很好。當時選角也沒有考慮過其他人,馬上就選定了他。

──導演主動提到了選角。您這次找的兩位主演,雷嘉汭、初孟軒剛巧在熱門影集《八尺門的辯護人》有合作過,在您選定兩位出演時本來就看過他們合作的作品嗎?請分享一點跟兩位演員合作的契機與互動。
馬:監製在看了《哭悲》(2021)後很喜歡雷嘉汭,並推薦了她。我們與她聊過不久,正好《八尺門的辯護人》播出,我看到她跟初孟軒的互動,覺得:這個 CP 我嗑了(笑)!影集不能完成的,那我的片子來讓他們談戀愛吧。
雷嘉汭飾演的小雯設定是 20 年前的人,我特別請她研究過去的說話方式。雖然年代差距不大,但她確實找出一種特別的腔調,或許觀眾會覺得奇怪,但正好呼應最後的反轉。而飾演阿嬤的滿嬌姨(王滿嬌)真的是很有經驗的演員,她知道孫子的設定是從國外回來,台語肯定聽不太懂,所以戲內戲外都刻意用台語跟初孟軒說話。初孟軒本身的台語好像也不太好,兩人就常常「有聽沒有懂」,自然就把祖孫之間的奇異感營造出來。
──「催眠」確實是構成這部片很關鍵的元素,電影開頭是催眠畫外音,結尾又收在男主角接受催眠治療。是一開始就打算用催眠發展,還是劇本創作的過程才嘗試加入的?針對這部分是否有做什麼田調?
馬:一開始的劇本其實只是單純的人鬼戀,完全沒有「催眠」概念。直到劇本初稿完成、徵求意見的階段,有朋友提醒我們:既然預算低、場景有限,是否該加入更有亮點的元素?最好是能與觀眾產生互動的東西。像《咒》(2022)就做到這點,也還沒有臺灣恐怖片超越它的成績。這讓我們開始思考,「催眠」或許能做到類似效果,又能呼應我很欣賞的導演諾蘭常玩的「記憶與夢境層層交疊」。
剛好我們家裡就有親戚是催眠師(笑),他從小也帶點通靈體質。我們向他做了大量田調,劇組許多人也親自體驗催眠。當然也安排了初孟軒與催眠師深聊、實際被催眠,並讓雷嘉汭在旁觀察。
催眠大致分兩種:一種是「探索」,另一種是「記憶回溯」。這部片子是把兩者結合應用。我主要用「探索」這個形式來框架整部電影,它進行的方式是鼓勵你四處想像,比方引導你上樓、下樓、推開一扇門,而每個人看到的都不同。片中李昂不斷探索,常聽到一個聲音問他「你還想不想繼續看?」其實就是催眠的真實做法。
「記憶回溯」則是我們劇組一位同仁真實的體驗。他在催眠前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我總是這麼沒有自信?」於是催眠師開始追問他最近一次沒有自信的時候,再一步步往回追溯:幾個月前、兩年前、五年前、七年前……最後回到童年的悲劇。當下他情緒崩潰大哭,甚至需要催眠師安撫。這段經歷啟發了我,也成為劇本的重要元素,就是大家在片中會看到李昂對小時候的自己說話。
──承上,催眠的元素帶來了一點難分虛實的效果,好像也給予了恐怖、詭譎場面多一層發揮空間。這怎麼幫助您思考、發想,營造具恐怖感的鏡頭語言及聲音設計?
馬:催眠的元素放進來後,我們在聲音設計上也做了很多暗示。比如時鐘聲,連結催眠時的計時;還有水聲,因為主角的母親在浴缸自殺,水象徵李昂的心魔,同時梧棲又靠海,所以我們在多處以水的聲響做鋪墊。
還值得一提的是,橫跨科學與玄學身兼我們催眠指導的這位親戚,同時還是這部片的音樂設計。他在配樂裡偷偷融入了催眠元素。雖然我不清楚技術細節,但我們確實利用環境音來營造近似催眠的感受。
也因此,我非常推薦觀眾二刷。當你知道這整部電影的情節真相,知道女主角的身分,再帶著全知視角回頭看,會有完全不同的體驗,也能發現我們藏下的彩蛋。

──臺灣恐怖片近年在市場表現上慢慢出現一些瓶頸,您怎麼看這樣的現象?您認為《詭鄉》這部片的新意、不同之處是什麼,也請再與我們的讀者推薦這部作品。
馬:過去 10 多年,臺灣恐怖片能在艱難市場中闖出成績,是監製和導演們努力的成果,我非常敬佩。雖然可能有人覺得鬼片有點千篇一律,但在我看來,我們找到很棒的特色,不管是挖掘民間故事,還是都市傳說,這是其他國家難以取代的。我相信這條路仍值得繼續發展,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土作品。
對我而言,《詭鄉》最大膽的嘗試就是「催眠」。這個概念其實很有風險,我最怕觀眾覺得「只是夢」,所以特別設計了大量指涉催眠的暗示來避免。我也會特別推薦這部片給喜歡「劇情向」恐怖片的觀眾,你可以跟著故事思考,發現一環扣一環的伏筆。
我們還有另一個嘗試,就是是以相對低成本探索可行的商業模式。能完成《詭鄉》,製片團隊真的功不可沒,大家動用許多人脈支援,在有限資源下把片子做到最好。因為我們相信,必須要能成功回本,才能有下一部,也才能繼續拍出更好的作品。
──若有機會繼續帶給大家作品,您有甚麼下一部的規劃嗎?
馬:其實我們確實思考了兩個方向,一是續集,以李昂的前女友為主角,發展另一個歸鄉故事;另一個是監製比較想做的前傳,從小雯展開,還發想了可以結合臺中「沙鹿六吊交替凶宅」的真實事件。大概有這幾個點子,都是期待發展出更龐大的「詭鄉恐怖宇宙」。■
.封面照片:《詭鄉》導演馬新語工作照;一群獨角鯨娛樂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