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影之間的歷史記憶:黃邦銓實驗影像中的口述與身體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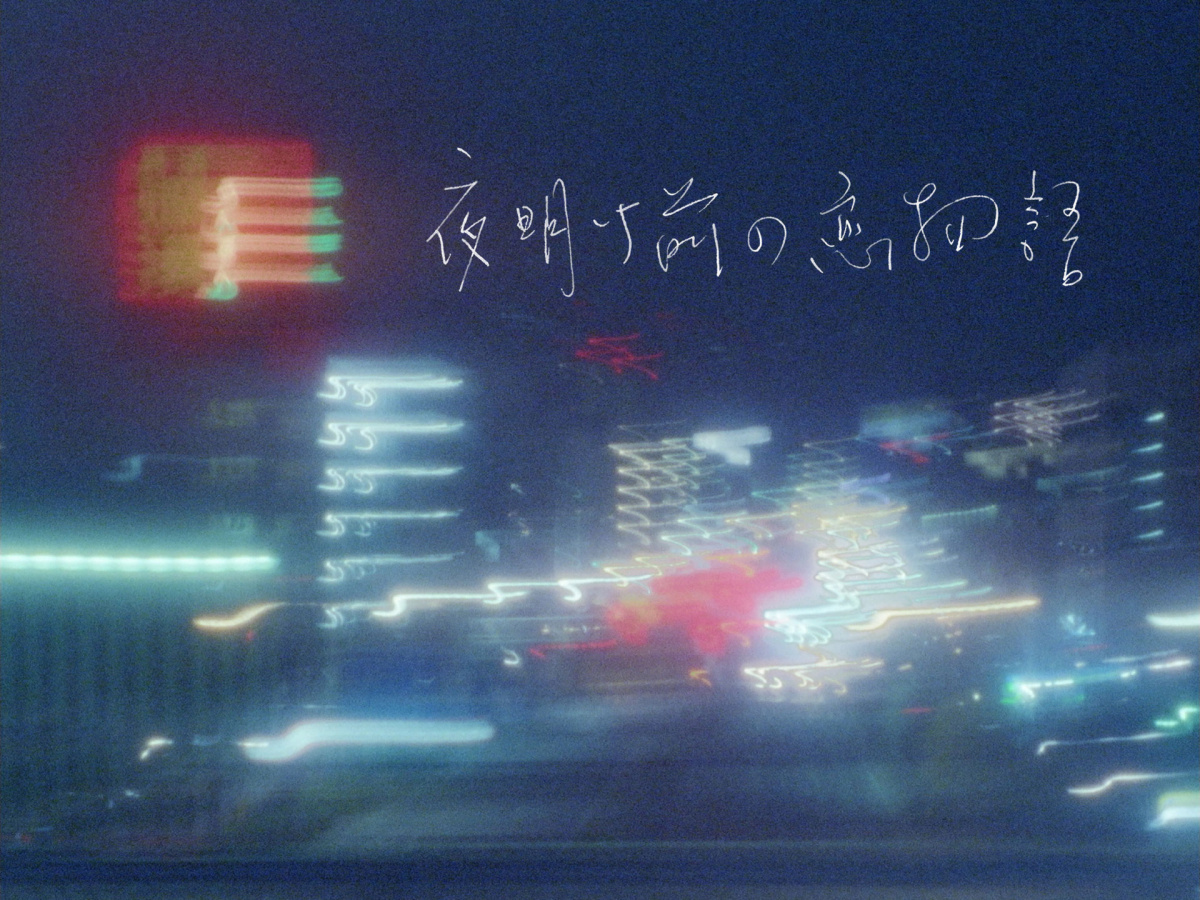
編按:臺灣導演黃邦銓長期以底片影像,進行對時間與空間的探索,其曾以《回程列車》與《去年火車經過的時候》兩度獲得法國克萊蒙費宏實驗競賽首獎,並在近年於導演林君昵合作完成《天亮前的戀愛故事》和《甘露水》等作品、系列計畫。本期《放映週報》刊載讀者投稿評論一篇,作者葉伊嘗試重梳黃邦銓作品,探索其創作如何進行對臺灣歷史觀念的回應與挑戰。請見本篇評論。
※※
在臺灣當代影像創作場域中,關於歷史與記憶書寫的作品屢見不鮮,但鮮少有如黃邦銓般,以極具詩意且實驗性的視聽語言,構築出介於敘事與檔案之間的影像詩學。身為影像創作者的黃邦銓,善於從歷史縫隙中發掘微小而隱匿的聲音,並將這些記憶的碎片轉化為兼具感官性與哲學性的影像文本。其作品如《回程列車》(2017)、《去年火車經過的時候》(2018)、《天亮前的戀愛故事》(2020)等,皆展現出對於歷史的深刻凝視與重新書寫的企圖。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黃邦銓電影中大量出現的「口述歷史」元素,不僅作為敘事的材料來源,更經由實驗性的影像技術與剪輯策略,使這些聲音從單純的紀錄語彙中脫離,進而與影像共同編織出一種深具詩學結構的「視聽檔案」(注1)。在這種語境下,歷史不再是被動再現的物件,而是可供感知、可被召喚與重構的過程。而身體──無論以鏡頭中主體或畫外音的方式出現,作為承載記憶與情感的場域,則成為黃邦銓電影中不可忽視的記憶載體。
本文將聚焦於黃邦銓實驗影像中口述歷史與身體檔案的交會,並試圖解答以下三個問題:一、實驗影像如何成為歷史敘事的替代語言?二、黃邦銓如何處理語言失效與記憶斷裂的狀態?三、其作品如何在臺灣影像文化中提供一種對主流歷史觀的回應與挑戰?試圖釐清黃邦銓如何以其獨特影像語法,重新發明歷史影像的文化與政治可能性。
聲影交織的記憶裝置:《回程列車》與《去年火車經過的時候》
黃邦銓的影像創作,根植於對離鄉背井與歷史記憶的長期凝視。面對那些未被主流歷史敘述所承認的聲音與碎片,他以實驗性的影像語法構築出一種「視聽檔案」的詩學政治,使個體記憶得以超越私密性,轉化為具有公共性的文化反思。這些材料既非純粹記錄,也非純粹再現,而是透過垂直蒙太奇、動靜態影像並置、或攝影術(底片顯影過程)等語彙,構成一種在聽覺與視覺之間交錯浮現的歷史書寫方式。當人們陷入回憶,影像便會顯現。於是,面對時間這個宏觀而不可抗的維度上,影像便成為對個人與集體歷史記憶一場「刻舟求劍」式的探尋。
黃邦銓的創作承襲了檔案電影與散文電影的傳統,卻又不囿於其既有範式。他的作品既具備日記電影的私密性與主觀性,也蘊含散文電影中對觀眾的召喚與對話潛勢。在這種架構中,發聲者不是全知的「上帝之聲」,而是一個具身的主體,在對「你」──觀眾──講述、分享、懷疑與踟躕。觀者被邀請不是作為純然旁觀的見證人,而是作為參與者,與影像一同追索記憶與歷史的皺褶。
這種「第一人稱的」重演紀錄片形式,也體現在他對「田野調查即電影」的實踐信仰上(注2)。影像不只是田調的結果,而是其本身的發生場域。黃邦銓以具身化的畫外音、非線性的剪輯節奏與感官性的聲響設計,讓歷史的語言不再只是理性論述,而是化為可感的氣流與質地,使記憶穿越時間之牆,在影像中斑駁顯影。他的技法演變始終圍繞一個核心命題:如何讓影像成為無法言說之物的見證與存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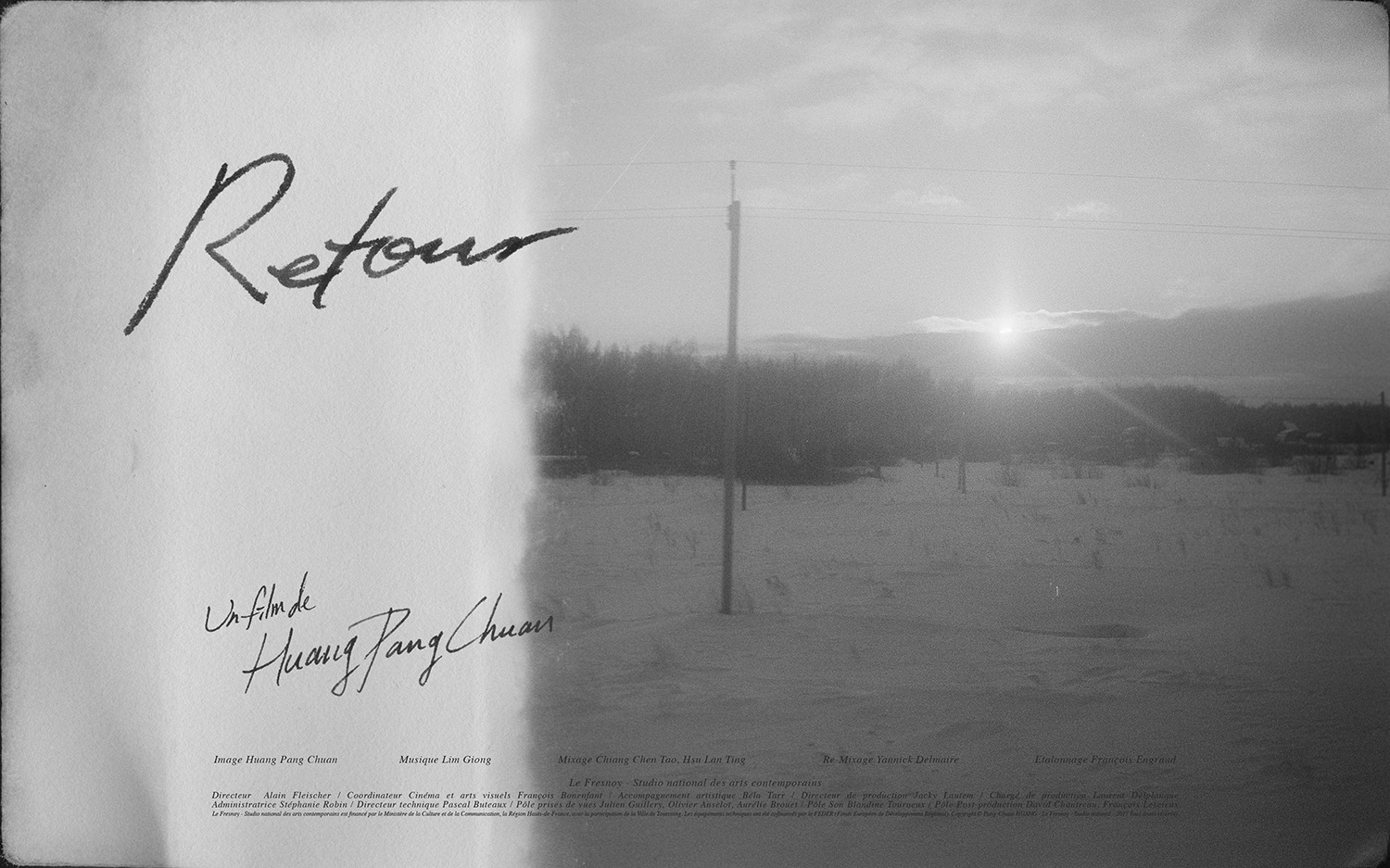
在《回程列車》(2017)與《去年火車經過的時候》(2018)中,黃邦銓展現出一種極具詩學意識的視聽實驗,藉由畫外音與畫面之間的錯置、疊合與斷裂,召喚個人與家族記憶,並以極具情感重量的敘述手法構築起一種「聲影互訴」的歷史敘事形式。這些作品不再仰賴影像的可視性作為記憶的唯一憑證,反而是透過畫外音的個人呢喃、歷史片段的語言召喚,與畫面之中流動不居的視覺元素交錯構成,打開歷史經驗的另一種感官路徑。
在《去年火車經過的時候》中,黃邦銓以彩色與黑白畫面的交錯切換,建構出一種明顯的時間分界:黑白象徵過去,彩色則指涉當下。然而,這樣的時間標記並非線性敘事的工具,反而在影像中形成一種模糊與流動的視覺感。伴隨著來自當地臺灣人的口述,影像並不急於為這些語言找到具體對應的畫面,而是在殘響的聲音與模糊的鏡頭中,讓觀眾與說話者一同進入記憶的霧區。這種視聽的不對位,使記憶既被講述,也被懸置,成為詩性的召喚而非歷史的證言。
《回程列車》則進一步強化了這種雙線交織的影像詩學。畫外音中,一位孫子講述自己關於祖父的記憶與返鄉的經歷,影像則在風景、靜物與火車行駛中構築出緩慢而深邃的節奏。深受塔可夫斯基作品中「自然力」的影響,這種對風、光、水等自然元素的凝視,也在《回程列車》中轉化為一種情感時空的肌理。例如在結尾處,畫面終於來到如今的海岸線,聲音卻召喚出過去祖父從對岸望見臺灣的記憶,那一刻,畫面與聲音不再分屬兩個時空,而是匯流於一種「或許曾經存在過」的歷史想像之中,使得畫外音的力量比拍到那個人本身還更有力道。
這種畫外音與畫面之間的詩學緊張,正是散文電影(essay film)結構中的關鍵特徵。如 Laura Rascaroli 所言,散文電影的本質不是提供答案,而是提出問題並與觀眾對話。其核心在於主觀性與自我反思的實踐──電影的敘述者「並非假裝發現事物,而是攤開自己」,而觀眾則被邀請參與這場公開而未完成的思索過程。《回程列車》與《去年火車經過的時候》中的畫外音,並非中立的解說者,而是具身化的個體,懷著記憶的不確定性與情感的斷裂說出自己的版本。這種主觀聲音的進入,也讓觀眾不再是旁觀者,而是進入者、感應者,與說話者一同編織對過去的追問。
此外,黃邦銓的影像敘事具有明顯的元歷史(metahistorical)(注3)與元批判(metacritical)(注4)特質。他不只是記錄過去,而是用畫外音與影像在時間上的分離,提醒觀眾這些敘事的建構性;站在畫外的創作者作為跨時空的全知者,選擇以聲音遁入每個獨立時空中當下人物的心靈角落,亦與銀幕外觀看的觀眾/聽者建立新的連結。他的電影像是在告訴觀者:「這些歷史不是你早已知曉的,而是你現在正與我共同創造的。」這樣的詩學手法,使得每一部作品都成為一場對遺忘的抵抗,也是一場對歷史再現權的重新分配。
身體作為檔案:《天亮前的戀愛故事》與黃土水紀錄片的詩學實驗
若說《回程列車》與《去年火車經過的時候》以聲音與影像的交錯召喚歷史與記憶,則黃邦銓與林君呢共同執導的《天亮前的戀愛故事》(2020)與為黃土水展覽所創作的《青春不朽》、《甘露水》、《久子》(2021)則進一步將「身體」作為歷史書寫的場域,透過手勢、動作、鏡頭語法與聲音質地的實驗,開展出一種感官化的記憶敘述。

在《天亮前的戀愛故事》中,導演藉由對臺灣作家翁鬧的追尋展開影像調查。影片中不僅側寫記錄受訪者口述翁鬧生平的段落,也透過影像實驗性地「重構」翁鬧的親身經歷──但特別之處在於,這並非傳統形式的重演或戲劇再現(例如由演員扮演翁鬧),而是一種主觀視角的構造。導演選擇以翁鬧的第一人稱視覺與聽覺經驗來呈現過往時刻,讓觀眾宛若「附身」在翁鬧身上,穿越時間進入那些被敘述者再現的記憶空間。這種主觀攝影與聲音環境的再建,讓影像成為歷史經驗的傳感器,使觀眾在觀看中不再是置身事外的旁觀者,而是與故事共振的知覺主體。
《青春不朽》、《甘露水》、《久子》等系列作品則聚焦於另一位臺灣歷史人物──雕塑家黃土水,尤其透過標榜為「臺灣史上最重磅的開箱」的敘事設計,記錄了黃土水雕塑遺作自倉庫被開箱、辨識、修復、展示的全過程。在《青春不朽》中,修復師的畫外音揭示了另一層歷史哲學:「修復的目的不是要讓雕塑回到剛被創作好的樣貌,而是要保留時間留下的痕跡,並阻止時間繼續腐蝕它。」這樣的語言其實與攝影的本質遙相呼應──將現實的某一瞬間以物質形式「定格」下來。黃邦銓的影像企圖不只是一種懷舊,也不只是對過往事物的保存,而是一次帶有強烈倫理意識的「延緩腐敗」行動:讓那些未被書寫的歷史不再無聲流逝,而是成為可被凝視、討論與思索的感官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天亮前的戀愛故事》與《青春不朽》、《甘露水》、《久子》皆出現了一種別具意義的鏡頭形式──動態拍攝的「全家福」或肖像照。人們或雕塑靜立於畫面中央,攝影機緩慢移動或凝視不動,從主觀視角延伸雙手擺弄著攝影機,營造出一種老式攝影術中「長時間曝光」的儀式感。觀眾此時被安排在「攝影師/見證者」的位置上,不是被動接受影像訊息,而是成為時間的參與者與歷史的共謀者。即便是在動態影像的敘事中,導演透過這樣的設計強調的是一種凝視與記錄的姿態──彷彿邀請觀眾一同完成這場記憶的召喚儀式。
這樣的影像策略使身體不再只是記憶的載體,更是歷史的書寫器官。手勢、觸摸、沉默的停頓、聲音的殘響與光影的閃動,組成一種詩學性的歷史見證方法。不單紀錄歷史人物,更讓記憶成為一種正在進行、可被重構的「開放檔案」。他邀請觀眾不只是觀看這些影像,而是在觀看過程中「與其共存」──在視聽交織的現場中,重新思考何謂被遺忘、何謂被看見。
視聽檔案的可能性:從紀錄到詩的轉化策略
黃邦銓的影像實踐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方向,將電影從傳統的紀錄工具,轉化為一座具備詩性與反思性的「視聽博物館」。在 Laura Rascaroli 闡述的散文電影理論中,這種電影形態並不追求敘事的完整性或事實的還原,而是在影片的第一人稱書寫中,打開了歷史、記憶與觀看之間的詰問空間。觀眾不再只是被動地接收資訊,而是被邀請作為參與者,在語言的空隙、影像的斷裂與聲音的殘響之中,建構屬於自己的歷史感知。
這種策略尤為適切地回應了當代臺灣面臨的歷史記憶保存困境。從白色恐怖的個人經驗到地方文史的邊緣敘述,許多歷史片段在主流的國族論述與官方資料體系中被省略、掩蓋。檔案資料的數位化雖提供了大量資訊存取的可能性,卻也時常落入去物質化的困境,缺乏一種與讀者直觀溝通的渠道。由此也可見,真正的博物館尚無法被資料庫或虛擬實境完全取代的原因,正在於它保存了物品的「時間靈暈」(注5)與「物質痕跡」,它們不只是資訊的載體,而是歷史能量的殘存體與觸媒,給予觀者震顫的現場空間。
而黃邦銓作品中對於「視聽檔案」的實驗性處理,也正是試圖透過聲音、手勢、鏡頭距離與素材質地的選擇,回復某種歷史經驗的「觸感」與「現場性」。例如,在《青春不朽》中對黃土水雕像修復過程的記錄,不僅強調雕塑本身的物質歷史,也藉由影像與畫外音交錯、參與者身體的勞動描寫,讓「修復」這件事成為對抗遺忘、延續記憶的身體行動。這些作品不是純粹的記錄,而是詩意化的歷史轉譯──像是某種流動的、具聲響與肌理的博物館,在觀看過程中召喚觀眾的感官與思考,成為歷史活化的參與者。
從這個角度來看,黃邦銓的實驗影像不僅拓展了檔案電影的表現可能,更在主流歷史書寫之外,開闢出一條記憶的側道。他讓影像不只是歷史事件的載體,而是回應歷史創傷、訴說被壓抑聲音的「媒介本體」;他讓觀看不再是接受,而是參與。這樣的電影,是影像化的抵抗空間,是關於歷史、感官與身分的另類書寫,也是臺灣當代文化 場域中,對記憶政治最詩性而有力的實踐之一。

梳理黃邦銓實驗影像的創作策略與文化意涵,他的作品不僅是實驗影像美學的延伸,更是一種對歷史記憶機制的深刻介入;美學的選擇並非只是敘事策略,而是更直指結構性的核心體現。從聲音與畫面的並置,到主觀視角的詩意重建,再到對身體與物質痕跡的凝視與重塑,黃邦銓以其獨特的視聽語法建構出一種「另類檔案」──一種不再依賴語言與紀錄,而是透過聲影交織、感官共鳴所形成的歷史再現模式。
在臺灣當代影像文化中,黃邦銓的作品佔據著難以忽視的特殊位置。不僅拓展了散文電影與檔案電影在本土脈絡中的實踐可能,更在記憶政治與身分認同的交錯地帶提出了倫理性的反思:我們要如何記得?誰被記得?誰又被遺忘?這些提問,通過他的作品,被轉化為視覺與聲音的詩句,在觀眾的感知中持續回響。■
.封面照片:《天亮前的戀愛故事》電影劇照;取自網路,僅作報導及評論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