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北影】不是水,不是火,不是土,而是「電」!──專訪《利貝拉達再一顆》導演寶拉托馬斯馬奎斯

里斯本街上古老雕像樹立,一台救護車臨停在社區大樓前,室內空間靜得像按下暫停鍵,一名男子躺在床上。當電流聲伴隨著畫面閃光,床上男子瞪大雙眼,空氣搖晃,身體分裂出疊影,直到在閃光中沒入一片白。
甫於 2025 第 27 屆台北電影節國際新導演競賽獲頒「評審團特別獎」的《利貝拉達再一顆》(Two Times João Liberada,2025)為葡萄牙新銳導演寶拉托馬斯馬奎斯(Paula Tomás Marques)的首部長片作品。本片以「意外之後」拉開序幕,描繪一部電影因意外被迫中止拍攝,擔任電影女主角的 João Liberada 則回溯起「意外之前」發生的種種。本片以片中片的形式,自由穿梭於景框之外──電影的景框與幕前幕後、舊時代的設定與現下時空的穿越,以及溢出歷史書寫/電影敘事的各種「無從詮釋」之現象。透過自由穿梭與反覆跨越,在景框與景框的縫隙間,交織出多重時間、多重歷史、多重視角的共存樣貌,並在這樣高度異質性場域中,建構出更細膩思考電影製作、銀幕呈現、異議者、酷兒與跨性別敘事的可能。而流淌於銀幕內外的友誼,也為本片鋪展柔軟的影像基底,與不需依賴任何敘事的自在自適。
──《利貝拉達再一顆》作為您的首部長片,以後設形式處理歷史與現下時空,是否能談談本片最初構想?
寶拉托馬斯馬奎斯(以下簡稱馬奎斯):我其實一直有在研究酷兒群體的歷史。就讀社會學碩士時,我開始接觸酷兒運動、性別理論,透過歷史理解性別理論脈絡。我讀《Caliban and the Witch》及其他女性主義文學書目,開始理解自己作為跨性別者的身分。那成為我研究酷兒歷史的絕佳時機,即便理性上是因為研究所的課業使然,其實更像個人而私密的探索。我會意識到這點,是我發現我想拍一部關於這些研究的作品,但我不知如何下手,因此你會在我畢業後拍攝的短片中發現一些蛛絲馬跡,如《Blindman's Buff》(2021)。
《利貝拉達再一顆》的最初構想稍早於我後來進「Elías Querejeta Zine Eskola」電影學院(注1) 的時間。我構想這故事圍繞於 João Liberada──受宗教審判記載啟發的虛構角色。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寫影片介紹,寫 João Liberada 的生命歷程。我去找 June João,這部片的女主角,也是我非常要好的友人。我想聽聽她的意見,因為我知道她能理解我的顧慮,也很願意參與這個討論。
我們馬上認知到這是奠基於暴力的書寫方式,因為這就是審判彰顯的面向。這些性少數經歷的苦難,處處是暴力。我對這種詮釋自然感到不適,也無比厭倦於跨性別者生命故事總是與暴力、苦難同義。因此,我們思考要如何以酷兒反歷史(queer counter history)視角介入,或帶入酷兒歷史的多種可能,這遠比透過暴力書寫建構角色故事有趣多了。所以我們就在想,不如把我們面對這些異端審判的暴力敘事,心中產生的各種疑問拍成電影。一切是這樣開始的。
有很多討論是發生在我就讀電影學院期間,畢業後這拍攝計畫仍持續著,也正好迎來一個很重要的籌備階段:找團隊。尋找能跟故事有所共鳴的夥伴──包括演員和劇組,是我們很在意的事情。我希望我們的成員是對故事有感。這點相當重要,也成為這部片的一部分。當我們理解到我們想透過 João Liberada 故事拋出的提問,拍一部電影,採取後設敘事便是必然,而尋覓團隊夥伴可以是切入後設敘事的一種方式。
《We Dead Awaken》(2022)、《聖潔的陶器》(Dildotectonics,2023)(注2)是在構思過程中完成的兩部短片,因此 June João 也出現在其中(在後者飾演較次要的角色)。《聖潔的陶器》的剪接師 Jorge Jácome,也是 June 很要好的朋友。我們在生活、工作上很自然而然地走在一起。本片製片 Cristiana Cruz Forte 則是從《Blindman's Buff》合作至今,我也擔任她畢製短片的剪接。參與這部片的每個人都有些緣分,大家因電影走在一起成為朋友。

──從您的作品當中,確實感受到團隊間的默契與照料,培養出社群連帶。想再回頭詢問研究相關的問題,是否能談談 João Liberada 這個名字?我意外發現 Saint Liberada,跟這角色有關嗎?
馬奎斯:Saint Liberada 是葡萄牙建國後出現的聖人,她是從葡萄牙天主教堂的聖徒史中遭到抹除的古代聖人。在其他國家,現今可能存在更多該聖人的相關記事,但其實主要發生地都是在葡萄牙。故事上是有些可相互對照之處,比方說 João 被 Franco 追求,而 Franco 與其他男人又被逮捕等等。聖利貝拉達在葡語又稱 Vilgefort,她之所以是聖人,跟她不情願踏入的婚姻故事有關。生前,她在違反意願下被安排一樁婚事,因此她向神祈禱,希望自己變醜,男人才不會慾望她。結果她長出大鬍子,男人就放她走了。因爲這個典故,她在一些地區為人所知,也因性別流動的狀態,被一些酷兒研究者視為潛在的酷兒聖人。這些都有關聯,但更相關的是,當你進入一間修道院,通常會得到一個源自聖人的新名。João Liberada 要成為修道院的一員,她得先獲得新名。這是我們角色塑造的思考路徑。Saint Liberada 的故事確實與 João Liberada 有所呼應,但很多人以為 João Liberada 就是 Saint Liberada,並非如此。僅僅是命名上的關聯性,帶出歷史典故,沒有其他深層含義。
João Liberada 的故事,主要跟其他性別異議者的審判故事有所連結,其中反覆出現的狀況是:暴力的身體檢查、妖魔化想像等。João Liberada 的故事也是不斷遭到騷擾的故事。且因她們是教堂逮捕的對象,在審判期間通常不會被視為受害者,情境比較類似於──在父權體制的視角下,女性激發了男性追求她們的慾望。此外,審判文獻中不只一次提及,被宗教審判所起訴的性別異議者希望被稱為「她」,而不是「他」──與出生指定性別吻合的代名詞。這些細節也集合成 João Liberada 的世界與角色形塑的一部分。
──那片中的版畫插畫是來自真實文獻記載嗎?
馬奎斯:那些都是波多藝術家 Daniela Lino 的創作。這些創作同時參考了來自中世紀和現代的各式版畫,其中也引用了中世紀獵巫手札的插圖設計。總之,它融合了多種元素。我們有一本版畫和插圖的參考目錄,我也針對每幅插圖希望代表的含義給予文字敘述。透過版畫的參考資料和版畫的符號體系與語言系譜,創作出這些版畫。有些創作可能更貼近原作。例如,《雌性曼德拉草》(The Mandrake Women)是一幅非常著名的版畫,與原作非常相似,但我們把臉置換成 João Liberada 的臉。
──電影結尾的版畫裡也加入了電影拍攝現場的元素。
馬奎斯:沒錯,我們想在過去、現在之間創造一些時間錯置的狀態。我們想把兩個時代融合在一起,並虛構出一個情境:電影的種種或許在過去便預見了──中世紀有某個插畫家,用版畫預示未來會有電影的拍攝,而這場拍攝將會受到 Saint Liberada 或 João Liberada 的鬼魂所擾。
──João Liberada 進到感化修道院──您之前的短片《聖潔的陶器》也有類似設定──這部分成為這部片滿核心的設定,正好感化修道院的故事也是片中導演所忽視的敘事。這也跨時空連結到現在時空下朋友聚會的場景。是否能分享您安排修道院場景的想法?
馬奎斯:感化修道院(reformatory convent)在葡語是 Casa de Recolhimento,或Recolhimento de Convertidas;在西語是 Casa de Recogidas。在伊比利半島、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地較為人所知。這些感化修道院不被認可為正統的修道院,通常修道院的人都來自貴族家庭和上流社會。感化修道院收容的是前性工作者、失去丈夫而遭社會遺棄的女性,或有罪需得寬恕之人(當然這是教會視角)。收容了尋求寬恕的邊緣女性,也因一些共同經驗指認出某種社群的存在。修道院經常被視為姐妹情誼存在的場域,但當我們談論的是感化修道院裡的邊緣社群,整個脈絡又不一樣了,這讓我們更想把它跟現代的性別異議者產生連結。其實,你是第一個問這問題的人。
酷兒、各種性別自古以來就已真實存在。只是主流史學抹除了這些故事,不讓它們流傳。這些故事被噤聲,無法成為古代、中世紀和現代史學的一部分。正如 Silvia Federici 在《Caliban and the Witch》所述,我們學到的歷史是由一系列重大事件組成,但歷史實際上是由大量小事件堆積而成的微觀政治學。歷史的書寫必然是更混亂的,因為它必須面對許多事情無法被具象化、被記載的事實。這跟電影也很相似,比方說傳統紀錄片有凝鍊現實的說法。但對我來說,沒有虛構就沒有電影。它離不開虛構──亦即文化遺產、觀點和文化意識形態。例如,《北方的南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1922)的完全虛構,讓我們反思迄今我們觀看所有歷史事件的方式,以及他者被呈現的方式。

──《利貝拉達再一顆》中,可以觀察到不同視角的共存,包括女演員的視角。
馬奎斯:這是自拍攝計畫之始就一直在進行的討論,包括拍攝情境中導演和演員之間的權力關係。June 有很多劇場經驗,她跟表演的關係很特別。在劇場,在首演前通常會歷經許多排練、討論的過程。而電影開拍前,通常只有一、兩次排練。所以在電影製作中,演員可能處於較不平等的位置,直到開拍才能完全理解這部片的內容,甚至導演有時不會花太多精力在深入傳達電影的理念上。
我說的不是角色塑造。我指的是讓演員充分理解電影拍攝背後的想法,包括演員在整個電影語境中的狀態,以及在這語境中扮演的角色。我覺得電影拍攝很容易出現一種情況是,你跟演員的初步接觸是奠基於你是否能演好這場戲,非你是否充分理解並願意進入電影的敘事及語境,這兩者截然不同。
這也關乎本片想傳達的事情。我們希望它能將演員在拍攝現場的脆弱處境呈現出來。正因如此,我們讓劇組出現在鏡頭前,因為這會讓這種脆弱性產生變化。我認為若能讓那些從未出現在鏡頭前的劇組,有機會來到鏡頭前表演,或許會是件好事。你會理解你的形體化為影像,以某種方式凝結、以物質狀態呈現是什麼感覺。站在鏡頭前真的是一種非常脆弱的狀態。有些人拍後設敘事,會請演員飾演劇組,但讓劇組真正站在鏡頭前,又會是截然不同的狀態。這部片不算後製團隊的話,至少每天拍攝的核心拍攝團隊都有出現在鏡頭前。
──在視角的呈現上,除了不同角色的視角,本片也納入各個電影製作階段的視角轉換。例如,畫面有時變成導演監看螢幕,能聽到導演和他人評論女演員演技的畫外音。有時又以色彩轉變指涉後製介入,有時則聽到讀劇的旁白聲音。
馬奎斯:要能深入理解這部片想拋出的提問,視角的呈現與轉換確實是關鍵,因為你很容易就把自己的觀點放入。要能抓到各種提問的核心,意味要設身處地思考,試著理解看待同一情境的不同視角。
電影確實可以產生某種「有意幹掉導演」,或以激進方式「摧毀導演地位」的傾向。但我們其實只是想讓導演稍微停下來思考和反思,而非真的想幹掉導演。某種程度上,我確實有自己的觀點,有我想要的拍攝方式,有我渴望表達某件事的迫切感。但團隊對話非常重要,因為這部片也是一部關於團隊合作、關於社群、關於他者的電影。所以我們跟劇組、演員初步接觸時,最重要的便是去了解他們是否能理解與認同這部片所開展的敘事及討論,以及我們如何找到一種相互理解和溝通的方式。
但電影同時也是虛構的。我從來不會要求人們得在片中「做自己」。我們一直將攝製視為一個虛構的過程。當我們開始思考人們在鏡頭前會如何呈現,我總會問他們是否想要一個新名字,還是保留原名。這件小事很重要,因為它讓人們明白,他們可以創造虛構的自我,也是一種保護的方式。
不同視角的呈現本身也是饒富趣味的。比方說,Saint Liberada 的「現身」,使用的語言都是時下用語,透過時空錯置撼動古人講話的刻板印象。
──這部片融合各種視角與語彙,我很喜歡這部片在視覺呈現上,在後設敘事與片中片之間斷點的銜接方式,彷彿斷點也成為敘事的一部分,而非只是揭露了幕後現場。片中也充分運用視覺元素,例如監看用的 Video Assist、調色,是否能談談視覺呈現的元素運用?
馬奎斯: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因為我想在一部片中融入多種語言。其中一種方式是在同一種語言中創造不同調性和層次,但同時又能以某種方式將所有元素融合起來。16mm 是最基底的語言,在構思初期我們就意識到片中片(時代劇)與幕後(後設片段)會使用非常相似的拍攝方式,才能順暢帶出這之間的流動變化。調色、音樂和聲音,則用來做出片中片與後設──及更細緻階段分野──的區隔。
挑戰在於如何在這麼多不同的語言間建立流暢的連結。我的剪輯師 Jorge 在融合不同媒材方面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他對於這方面的擅長也可從他的作品一窺其貌。例如,背景音樂既有音景,本身自帶影像美學,就像電流在片中自然流動。它可以如鬼魂般附身於片中,又不失趣味。我認為這些都是串接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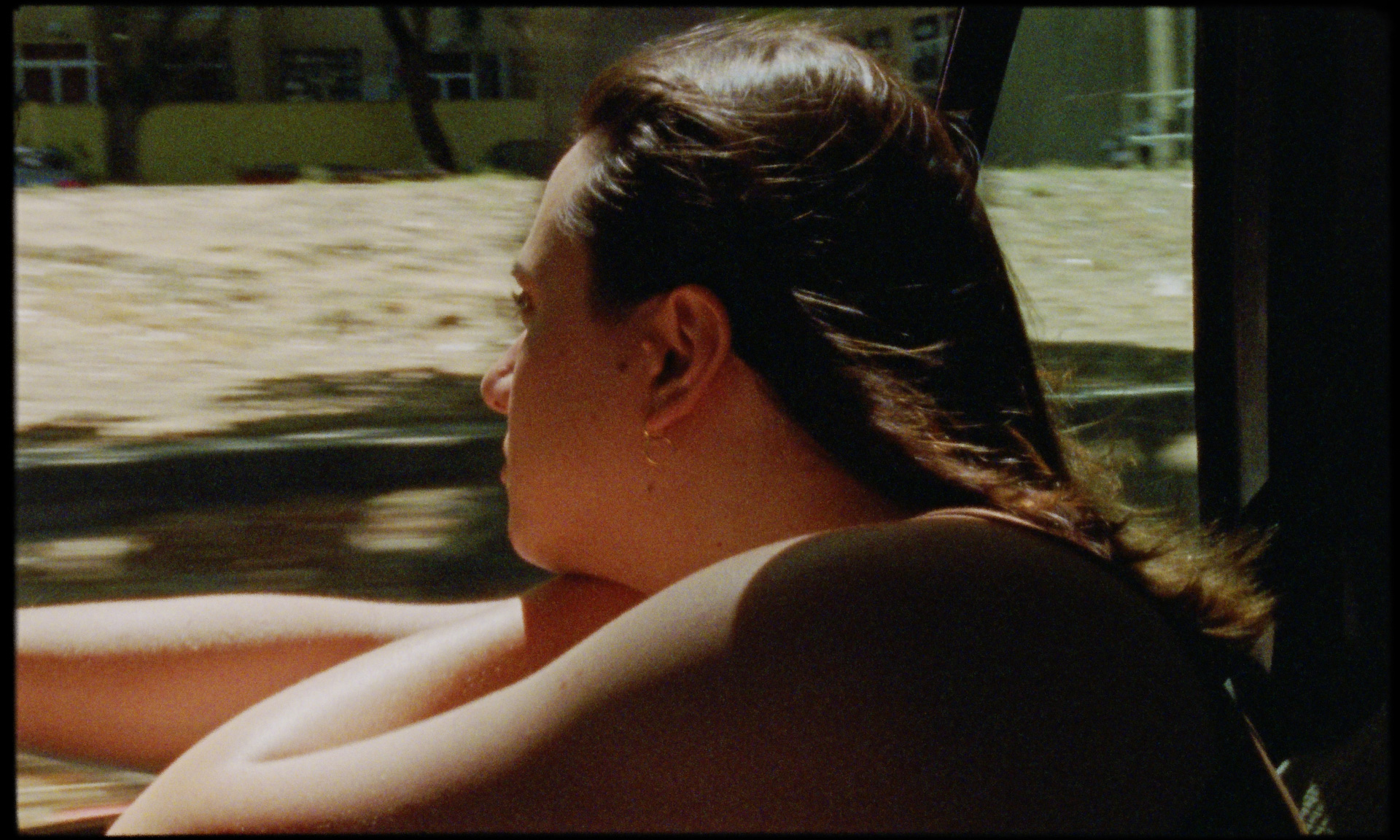
──全片都是用 16mm 拍攝嗎?是否能談談你的工作方法?
馬奎斯:除了 Video Assist 之外,所有都是用 16mm 拍攝。我會非常執著於計算自己用了多少膠卷,每一秒都精打細算,比方說我會算空景大概都拍 30 秒,多數場都只拍一兩顆鏡頭。我會算得很精準,因此我若能在每顆鏡頭中減少一些秒數,我就知道我可以有些餘裕做更多實驗與嘗試。
我覺得我用膠卷拍,能比用數位拍更多東西,因為我把所有東西都算好了。拍完那顆鏡頭,你也無法再浪費膠卷,因此你會有時間去想其他事情。不會一直拘泥於某顆鏡頭、場景,且會更加專注於每顆鏡頭。拍攝時,我更多時候是在思考剪輯而非構圖。這可能也跟我拍攝養成有關,因為我一開始是學膠卷是用 Bolex 攝影機拍,它只能連續拍攝約 25 秒,所以我總是在思考如何斷點,如何在各個想法之間建立連結。Bolex 攝影機的使用與拍攝養成,讓我對拍攝和分鏡製作養成不太一樣的思考方式。
Video Assist 的部分,我們是到剪接時才確定要用它。在拍攝現場,我們有個很爛的 Video Assist。我們沒有每顆鏡頭都用,因為團隊規模很小,用 Video Assist 會拖慢拍攝節奏。我們使用它,單純只是想知道現場正發生的事情。但它總是出問題,且又黑白畫面,搞得像鬧鬼一樣。因為這樣的特質,我們在拍攝過程中,便開始討論那些畫面是否能在剪接時用上。我曾想嘗試 DV 夜視模式的美學風格,帶有恐怖片感。某種程度上,Video Assist 最能夠接近我們原本想要的夜視效果。
──您的電影融合很多元素和風格,有時甚至覺得閃現大衛林區式的時刻,例如片中使用閃光的方式。
馬奎斯:用膠卷拍攝很自然地會呈現這種閃光的狀態。當我看到毛片時,我就知道我會保留這些閃光。我知道它們會成為這部片重要的美學風格。《聖潔的陶器》中也有這些白色閃光,但它還未被作為一種語言、一種如電的美學來探索。當我看到毛片時,我意識到這部電影的核心元素不是水,不是火,不是土,而是「電」。想到林區不是沒有道理,我和 June 在寫劇本時,她便經常談到林區。剛好我在編劇階段看了《雙峰》(Twin Peaks),我之前沒看過。但當我思考「電」作為電影的元素時,我並沒有想到大衛林區。若用這樣的方式反映在片中,蠻有趣的。■
.封面照片:《利貝拉達再一顆》電影劇照;2025 台北電影節提供
